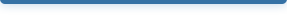综观人类历史上文明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历程,宗教、战争和贸易是三大主要途径。意大利与中国在地理上处于欧亚大陆两端,遥遥相望。在现代之前,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宗教和贸易则成为双方主要的交流领域。意大利人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其特定的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所塑造的民族特点,使他们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扮演了活跃的先锋和主力角色。
中西交流之初,古罗马与中国的往来大多仅存单方面史料,缺乏互证。例如,根据《后汉书》《晋书》记载,罗马使节于公元166年、280年至289年曾经到达中国。然而,罗马方面却没有史料加以印证。根据罗马史料记载,奥古斯都时代,一个来自“丝绸之国”的使团曾经到过罗马,但中国史料却没有提及。可以确证的事件是公元97年受班超之命,甘英原本要出使罗马帝国。他到达了波斯湾,却没有继续前行,也许是当时控制交通要道的安息人的劝阻导致其折返。
由于空间上的距离,素未谋面的中西方之间形成了某些神话和传说,人们将自己对黄金时代的思念和对乌托邦幸福的渴望,寄托在遥远的民族身上。中国人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其人质直,市无二价”。在通往大秦的路途中没有匪徒,他们任命三十六位元老商议国事,立贤者为王。而罗马人称中国为“丝绸之国”,中国人非常高大、红头发、蓝眼睛,他们不知天主,长寿可达几百岁。此种想象与实际出入较大,但双方均以对自身的文明自信为基础,又对大陆另一端怀抱某种广阔胸襟和探知欲望。
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经中间商口耳相传甚至有意曲解的认识得以部分纠正,对东方的重新认识也成为西方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催化因素。在后世史书里,该时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人非马可·波罗莫属。其实,他只是若干担当中西交流媒介的意大利人中的一位。宗教方面,来华传教的主要人物均来自意大利。若望·柏朗嘉宾于1245年启程来华,回到欧洲后编撰《蒙古史》。若望·孟德高维诺则以教宗特使身份,于1290年从意大利出发,经海路到达中国,觐见元成宗后未曾离开,直至年逾八旬去世,墓碑至今留存泉州。
在贸易方面,1255年泉州海关官员赵汝适编撰《诸蕃志》,其中记载了西西里岛的部分情况。而根据西方文献的记载,在来华的意大利商人中,有名字可查的包括若干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其中有人甚至迎娶了中国女性,在华定居,终老于此,扬州还曾出土这些意大利人的墓碑。14世纪,一位佛罗伦萨银行职员将自己和同事们的工作经验,整理编成一本名为《买卖手册》的书籍,为前往世界各地的商人介绍如何旅行,其中就包括他从未到过的中国。尽管如此,马可·波罗仍是该时期中西交流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位意大利人。他留下的游记刺激了欧洲的世俗欲望,催生了地理大发现。
马可·波罗不会想到,他的举动间接导致意大利逐渐失去其坐享了几个世纪的繁荣,欧洲的金融、贸易中心不再专属于意大利,中西交流的贸易途径也开始被其他欧洲国家开拓和垄断。不过,意大利人继续掌握着宗教途径。耶稣会会士在中国的活动之所以能有所突破,要归功于几位灵活行事的意大利人。例如,范礼安于1578年9月到达澳门,随后他认识到,葡萄牙和西班牙诉诸武力、枪炮的思维并不可取,这两国的宗教人员深受国家利益、种族偏见和僵化思维所左右,不易妥协,对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化不感兴趣。于是,他向上级会院请求,调两名年轻的会士来澳门学习语言,还坚持要求必须是意大利人,他们因其性情和文化背景而没有民族主义偏见,比较适合担此重任。利玛窦因此被派至澳门,并以实践证明了范礼安这一选择的正确性。
在利玛窦之前,意大利人之所以在中西文明交流过程中占据主力位置,基本上是因为他们长期处于西方世界的“中心”。古罗马帝国的辉煌时代自不必赘述,他们那时正处于西方文明的第一个鼎盛时期,面对东方,他们具有天然的话语主导权。“大秦”这个称呼最初由中间地带的中亚民族所创,意为比秦国(中国)更辽阔、更强大。经由中间商的交流,中西双方对彼此的印象更像神话和传说,但这是基于各自实力和政权稳固的平等想象,且双方文明的发达程度足以支撑这种平等的、想象模式的交流。不仅如此,间接的物质交换同样仰赖双方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古罗马人也许对中国人的外表认识有误,却对中国的丝绸非常熟悉。罗马帝国每年造币总数的一半都流向了东方贸易市场,罗马人强劲的购买力使其成为西行丝绸最大的消费群体。
4—10世纪,希腊文、拉丁文资料对中国的印象基本上停留在古罗马时期。13—14世纪中西交流有所进展,这也正是意大利历史上的另一个辉煌时期。地中海商业空前繁荣,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具备促进中西文明交流的重要经济基础。以马可·波罗的出生地威尼斯为例,10世纪时,威尼斯已拥有远洋舰队,并取得了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而后几乎完全垄断了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港口以西的运输贸易。在十字军东征的年代,威尼斯在为军事活动提供运输和物质保障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厚报酬,同时也借机扩大了商业势力范围,迎来迅猛发展时期。其实,除去战略、地理位置优势以外,威尼斯并无更多凭借,却建成了集发达的呢绒业、丝织业、造船业、兵器制造业等于一身的海上强国。这些亚平宁半岛城市国家的繁荣,使得意大利在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方面面临极大挑战,但是也为意大利人长期担当中西文明交流的主力军角色提供了机遇。这些城市的居民对封建桎梏更加漫不经心,而对灿烂的西方古典文明更为热情。他们不因对某个王权的效忠而浴血沙场,更愿意纯粹地忠于商业利益或者宗教信仰。
马可·波罗背靠强大的威尼斯,践行了中西文明交流的贸易途径。另一位杰出人物利玛窦则践行了宗教途径,其背后是意大利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传统。但是,利玛窦的作为不单单具有宗教意义,正如马可·波罗虽然集中体现了地中海资本主义萌芽背景下的商业扩张动机,其意义却也不局限于物质利益和经济发展一样。
首先,意大利历史具有复杂性与统一性。一方面,长期以来,亚平宁半岛上四分五裂、邦国林立,各城市国家在政治、经济利益推动下彼此混战,企图通过内部斗争建立最高权力,显得水火不容,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压倒性战胜另一个。另一方面,他们又存在血缘、文化、家庭生活、政治、经济、宗教行为等多方面的统一性,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虽无法完全分裂,但也不能顺利建立统一的独立王国。多样性是意大利的优势,奠定了意大利人承担中西文明交流使命的基础。其地方认同和宗教认同长期高于后来形成的民族国家认同,他们不易被民族主义偏见和国家利益认同所左右,因此更乐于与遥远的东方文明进行交流。
其次,罗马的历史传统和人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意大利人形成对另一种文明的相对开明、包容的态度。诚然,这种态度背后受强烈的目的驱使,他们青睐灵活、务实的手段,冷静地关注着实际问题和局势,具有现实主义特色。利玛窦便是该特色的经典范例。他在意识到“西僧”身份不利于实际行动时,立即改换旧例,“合儒易佛”。他的上层路线以及文化策略,都建立在对中国语言和文化深入认识的基础上。他具有政治远见,懂得外交妥协,他所使用的手段甚至可以在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的思想中找到源头。他们都认为,无论个人或国家,争取成功是绝对必要、唯一正确的目标。
综上所述,悠久而厚重的历史积淀促使意大利人形成了相对开放的文明观。而其国家统一进程的迟缓,尤其是强烈的地方认同和宗教认同,使得意大利人长期不受民族国家意识的影响,而是从现实利益出发,灵活运用各种策略以达成宗教和商业目的,从而成为13世纪和16世纪两次中西文明交流繁盛时期的先锋和主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