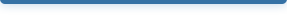中国过去没有建立自己的“古文书学”学科。虽然早在1914年黄人望编《史学研究法讲义》时已经提到古文书学(此承侯旭东先生惠示),但那不过是摘译介绍日本古文书学的内容而已,在此后的史学界影响甚微。直到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古代史研究所)几位研究古文书的年轻同仁倡议开办“古文书研究班”,才揭开了建立“中国古文书学”的序幕。2012年第一届“中国古文书学学术研讨会”在历史研究所召开,标志着“中国古文书学”正式建立。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立项,标志着“中国古文书学”得到学术界支持和国家承认。2020年末这一项目大致完成,2021年3月1日召开了结项会议,标志着“中国古文书学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关于“中国古文书学”在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支持后的进展与成果,已有文章做了详细介绍。本文结合个人研究,谈一谈“中国古文书学”的研究特点和今后发展。
加强“中国古文书学”的理论探讨
所谓“中国古文书学”理论,主要包括探讨和定义“文书”“古文书”“古文书学”,“古文书学”研究的性质、对象、范围、视角、方法、特点,以及与档案学、古文献学、历史文书学的区别等方面。
我曾在《关于“中国古文书学”的若干思考》中指出,古文书学意义上的“文书”应该具有的性质或特征是:第一,它是未经后人改动过的原始资料。第二,它不包括各种撰写或编纂的典籍。第三,它一般是用文字书写的。第四,它以发件人向收件人表达意图者为主,同时包括帐簿等经济文书。第五,它应具有完整格式,例如牒、状类文书一般应包括发件者、收件者、结尾用语、日期等要素(《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此前在《“中国古文书学”:超越断代文书研究》中,关于古文书的定义我还写过: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的主要是出土或传世的、近代之前的文书资料,“以手写为主,基本不包括雕版印刷的文献,但若有文书集成或文书档案类刊本,似亦可包括。至于材料,则不论甲骨、青铜器、简帛、纸张和砖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25日第5版)。对此定义,有学者特别是研究明清古文书的学者认为,明清古文书很多都是刻印的,因此对“古文书”的定义不能局限在“手写”上。这一意见是有道理的。我想定义“文书”的关键是看它有没有保留文书格式,因为“格式”是“文书”的灵魂,如果去掉格式,文书就与文献没有区别了。所以,那些刻印的文书如果具有完整格式,或者与原始文书保持一致,似乎就可以将其定义为“文书”。
关于“中国古文书学”与日本古文书学的异同,我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表现在古文书的来源上。中国古文书有出土与传世两大来源,而日本主要是传世文书。第二,表现在古文书的类型上。由于权力结构不同,日本古文书的类型更为复杂。近来有学者认为将文书刻石留存,也是中国古文书学的一个特点。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李雪梅《中国古代石刻法律文献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收录从战国到清末石刻文献8223种,其中公文碑占很大比例,如唐宋金元时期,公文碑在同期法律碑刻数目中占比高达三分之二,仅蒙元时期的圣旨碑、公文碑就有193份。这些公文碑完整保留了公文格式,包括敬空、提行、印章、画押等,显然就是古文书的原样镌刻。以刻石方式如此大规模、多地域、多场合地保存古文书,确是“中国古文书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总之,关于“中国古文书学”的定义、特点等理论问题,今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从“古文书学”视角研究古文书
所谓“古文书学”视角,就是采用符合古文书特点的角度,从文书的格式和语言、运行方向和规律、附属要素如署名印章画押,乃至文书的物质形态等各方面进行研究。
例如研究诉讼文书格式,可知唐代因等级不同分别使用了“辞”和“牒”。“辞”的格式特点是年月日姓名及“辞”置于首行,且有受理官司名称,最后有“请裁,谨辞”类套话。“牒”的格式特点是年月日姓名置于末行,没有受理官司名称,在“标的”之下以“牒”起首,结尾有“请裁,谨牒”字样,最后在姓名下复有“牒”字。“辞”和“牒”的内容都可以称为“状”,后来就出现了用于诉讼的“状”文书。这种“状”同时含有“辞”和“牒”的特点。随着“状”的逐渐普及,“辞”变得少见,“牒”也逐渐被淘汰,结果就是“状”取代了“辞”和“牒”,成为后代诉讼文书的主要类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4卷)。学术界以往对文书格式特别是公文书格式有很多研究,其特点是宋代以前以复原文书格式为主,宋元以后以分析文书格式的复杂构成为主(《中国古文书中的公文书样式研究综述》,《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9辑)。
再如从敦煌吐鲁番文书出发研究契约文书中表示其真实性的方式,发现在近500的时间内,其方式依时代不同主要有三种:第一阶段的用语特色是“各自署名为信”,主要行用于高昌国时期。契约当事人主要采用署名方式。第二阶段的用语特色是“两和立契,画指为信”。从唐贞观二十年(646)前后开始出现,一直沿用到9世纪中叶。第三阶段的用语特色是“恐人无信,故立私契,用为后验”,从唐末五代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年,采用的具体方式主要是画押(《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8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特别是“画指”(画出中指3个指节)的出现与普及意味着什么,值得今后继续进行研究。
古文书物质形态方面还有如纸张研究。日本古文书学者对此十分重视。例如日本中世纪有一种传达天皇旨意的文书,纸色很重(往往是墨绿色)又很粗糙,被称为“宿纸”(再生纸)。为何会用这么粗糙的纸呢?原来在天皇旨意下达的流程中,先要由“蔵人”(天皇秘书)承受天皇“口宣”,将“口宣”记录下来,做成“口宣案”,非正式地传达给受书人。换言之,这种再生纸文书原不过是天皇旨意的笔录(小岛道裕《中世の古文书入门》2016年)。明白此点,则只要看到用这种颜色很重很粗糙的纸做成的文书,就能了解其运行程序和所起的作用了。中国古代对文书用纸也有明确规定,例如唐代诏敕一般用黄麻纸和黄藤纸,赦书则用绢黄纸之类。用纸之外,印章的使用也值得研究。一般而言,文书的印章钤在日期上,是要保证文书发出时间的准确性,以检查文书处理是否有所延误。还有一种钤印,是在文书上“随处印署”(北宋《天圣令·杂令》)。这是一种怎样的印署?值得研究。还有学者提出要把“人”的因素纳入古文书学的研究范围,那当然是更高层次的追求了。

宣传和普及中国古文书学
中国古文书学自建立以来,为宣传和普及这一新兴学科,我们每年一次,先后召开了8届古文书学学术研讨会,其中有3届分别是与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和邯郸学院合办的。我们还与中国政法大学共同主办了2次“古文书学研习营”。这些活动宣传普及了“中国古文书学”的理念与知识,使更多学者加入“中国古文书学”的研究队伍中来。
为了普及古文书学知识,让历史研究者和学习者知道什么是古文书、古文书的形态如何、怎样阅读和理解古文书,我们编写了《中国古文书读本》(以下简称《读本》)。《读本》将先秦到明清的古文书大致分为5类(官府往来文书、契约文书、帐簿文书、诉讼文书、书信文书),然后在每类文书中选取若干,介绍给读者。为使读者对古文书有个整体概念,《读本》在每个断代每类文书之前都有“总论”和“小序”,介绍本断代本类文书概况。每件文书先给出图版,以及该文书的录文,然后进行“注释”和“解说”,解释难解词语,解说文书出处、材质、尺寸、内容、价值等,最后给出有关该文书的参考文献。有此一书,读者对于中国古代文书的基本样式和特征就能了然于胸。《读本》可以说是“中国古文书学”的入门书。
今后在普及中国古文书学方面还可以做以下工作。第一是继续编写古文书入门书,并像日本学者所做的那样,将上行、下行、平行文书都用图示方式标出文书的发出者、接受者、结尾用语、署名等级、日期印章等,让读者能够直观地读懂文书。其实,国内特别是明清文书的研究者已在使用图示方式分析文书的结构(参见沈蕾《清代官府往来文书的装叙结构分析》,《档案学研究》2019年第3期)。这样的图示图解方式,对于初步接触古文书的读者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第二是编纂古文书用语辞典。现在关于古文书的语言辞典,国内只有刘文杰编写的《历史文书用语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但仅有“明·清·民国部分”。今后应该组织力量编写一部从战国秦汉直到明清的古文书用语辞典,以方便学者习读各个朝代的古文书。第三是争取让“中国古文书学”进入校园,成为学习古代史的学生在史料处理方面的基础课。只有这样,才能在大学普及古文书学知识,使历史学系学生面对古代史料时能多一种视角,自觉运用古文书学的方法研究古文书进而研究历史。
中国现存古文书有百万件之多(还不包括清宫档案),如何运用古文书学的理论、视角、方法去处理这些文书,并通过这些古代曾经实际使用过的文书来揭示当时“人”“事”“物”的流动,乃至历史过程的方方面面,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希望有志于此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加入古文书研究的行列中来,加入了就会发现这其中别有洞天,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中国文字博物馆 资料图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