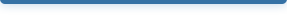有辽一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向来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然而因为史料匮乏,许多问题都存在争议,很难达成共识,但关于五京道制度似乎是一个例外。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接受的是《辽史·地理志》的概念,即五京道是辽代的一级地方行政区,五京为各自区域内的行政中心,作为地方长官的五京留守统领一道的军政大权。然而,近30年来这个常识开始受到挑战,一些学者撰文对《辽史》记载的五京道制度提出质疑,而另一些学者则坚称辽朝确实存在五京道。辽朝“五京道”的存否就此成为辽史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辽朝存在“五京道”。谭其骧认为辽朝“地方行政区划,道以下一般为府州军城与县(城)两级”,他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辽代部分即以五京道为一级政区分别绘图(《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时期》,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杨若薇也认为辽朝存在五京道,道的长官诸京留守为长期固定的地方要臣,“总揽一方军、政、财诸大权,坐镇一方,几拟于人主”(《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傅海波、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谓“1044年,当云州(今大同)升为西京时,地方行政管理体系通过以五京为中心的道而告完成”。
有些学者虽然承认辽朝存在五京道,但对“道”的行政长官提出疑问,认为诸京留守并非“道”的行政长官。周振鹤认为,辽朝虽然存在五京道,但其形式比较特殊,道为一级行政区,却并未设置明确的一级地方政府,也没有明确的道一级的行政长官(《中华文化通志》第4典《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显然,他并不认为诸京留守是五京道的行政长官,但对这个问题却没有表示更明确的意见。台湾学者杨树藩根据《辽史·百官志》关于三京宰相府的一条记载,推测辽代五京各有一宰相府,为五京道的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为左、右相和左、右平章事;宰相府下设留守司、总管府、警巡院等机构,分别掌管一道的民事、军事、治安、财政等(杨树藩《辽金地方政治制度之研究》,台北宋史研究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11辑,1979年版)。李锡厚亦认为五京是各自所在地区的行政中心,五京道是真实存在的,由诸京宰相府及各职能部门统辖诸道(《论辽朝的政治体制》,《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两文观点虽然新颖,然而其立论的依据显得过于单薄,未能得到学界认同。
学界出现辽朝根本没有五京道的说法之后,一些学者继续撰文,从不同角度论证辽朝存在五京道。傅林祥首先提出了一个比较大胆的说法,辽五京的留守司属于中央机构,留守司的官员是京官,而非地方官员,以五京直接管辖地方州县,是辽朝地方行政制度的一种特殊形态。他认为五京诸区相当于元代的中书省辖区、明代的南北直隶区域,并不是地方一级行政区,也没有相应的行政机构(《辽朝州县制度新探》,《历史地理》第22辑,2007年)。李锡厚认为元人所修《辽史·地理志》脱胎于辽人耶律俨《实录》以及金人陈大任《辽史》,五京道的编排方式并非元人向壁虚构,而是渊源有自。他复又胪列《辽史》“三京诸道”“南京道”“诸道”等记载,认为辽朝存在五京道及相应的管理机构(《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何天明则认为辽朝行政区分为五京,监察区(准政区)分为五道,“道”是为“特殊政治目的”而设的地方政区(《辽代五京与道级政区析疑》,韩国檀国大学北方文化研究所《北方文化研究》第6卷,2015年)。张韬通过梳理文献、石刻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辽代先后建有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道级行政区划,该区划是实行于插花地(汉人、渤海人及部分女真人、党项人、吐谷浑人、兀惹人、高丽人杂居之地)、纯农耕地区、部分草原地区的一项地方行政制度(《辽代道级行政区划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辽朝不存在“五京道”。一些学者主张辽朝根本不存在道一级的行政区划,甚至认为五京道纯属子虚乌有。清人吴廷燮在《辽方镇年表》中已隐约表达出辽朝并不存在五京道的想法。他指出,辽代某些节镇与诸京留守府实为平级,相互之间并无隶属关系,这无异于否认了五京道为辽朝一级地方行政区的传统观点。20世纪80年代,李逸友首先明确提出辽朝不存在统一的“京道”体制。他认为在汉人聚居的燕云地区,确实存在着管理国家州县的“京道”,但在上京、中京和东京地区,因大多是私属性质的头下军州与隶宫州县,并不隶属于京道,《辽史·地理志》把这些州县列入上京、中京、东京道,“只是表明这些政权机构和城郭所在的区域,并无‘道’一级政权”(《辽代城郭营建制度初探》,《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他虽然不同意五京道为全国范围内的一级地方行政区的传统观点,但并未全盘否定辽朝存在京道一级的政区。
彻底否定五京道存在的是张修桂、赖青寿的《〈辽史·地理志〉平议》(《历史地理》第15辑,1999年)一文。在他们看来,所谓的五京道实际上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辽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五京府在地方上的实际地位与节度、观察等方州及节度使部族相埒;《辽史·地理志》之所以要采取五京道的编排方式,乃是援引两《唐书》《五代史》的惯例,以“京道”为总纲,罗列州县,这只是出于谋篇布局的需要。不过,该文并非专门讨论辽朝的五京道制度,这一看法也并未引起辽史学界的重视。
此后,关树东撰文讨论辽朝地方行政制度中的“京道”问题,引起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他力主辽朝不存在所谓的五京道,《辽史·地理志》所记载的五京道乃是出自元代史官之手,并不能反映辽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在辽朝文献及石刻资料中没有依京划道统辖州县的记载;辽朝只有八个财赋路,除此之外没有路一级的行政区;辽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沿袭唐末五代制度,实行府、节镇州—防御、观察、刺史州—县三级制度,“辽代的府、节镇州始终是真正的高层政区”(《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上述观点的提出,使传统的五京道制度说法受到动摇,促使学界更为深入探讨辽代地方统治的权力结构。
辽朝存在职能有限的“五京道”。康鹏认为辽朝确实不存在作为行政区划的道制,但很可能存在军事性质的道(路)。至少在南京、西京、东京地区,应当存在道(路)一级的军事机构,即南京道的南京兵马都总管府、西京道的西京兵马都部署司、东京道的东京兵马都部署司。至于上京和中京地区是否存在道(路)级军事机构,仍需进一步研究(《辽代五京体制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余蔚认为“辽之五京,除了作为首都、陪都之外,同时也是地区中心”,辽朝的财赋“路”、军事“路”虽然实际存在,但是“道”也不是虚指。辽朝“五京道是实际的存在,有其实际的功能”。“‘道’与‘路’在称法上并无截然区别,‘道’是作为财政区划‘路’的前身”。“辽有三个高层区划体系,财政‘路’、军事‘路’与民政‘道’,‘道’的功能最为多样,但最关‘行政’之事,然而不能覆盖全境。而财政、军事两种路,又非正式的行政区划”(《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陈俊达认为《辽史·地理志》所言的“五京道”应当是一种监察区,与“军事路”“财政路”在地域上存在重合,呈现出向行政区过渡的趋势,与节镇日渐形成一种准行政隶属关系,但是这一过渡最终未能完成,辽朝自始至终实行的是节镇—州—县三级行政区划(《辽朝节镇体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
以上种种认知,无疑提醒我们,辽代地方的统治结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辽朝是否存在“道”一级的正式机构,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