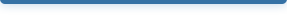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论文提要]:本文通过对华严译籍中一些单行本和集成本的比较研究,探讨了华严经学从释迦崇拜到多佛崇拜、再到卢舍那佛崇拜的具体演进过程,并从一个侧面揭示华严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般若学的某些交涉和关联。本文认为,在华严类典籍中,“释迦分身”、“十住行佛”和“法身分身”是其提出的多佛存在的三种类型;普贤境界是其展现的成佛样板;卢舍那佛是其塑造的信仰新对象。华严经始终依据基本教义发展的需要塑造崇拜对象,构建信仰体系。
[关键词]:释迦分身;十住行佛;法身分身;卢舍那佛
一、问题提出
从佛教创立到大乘佛教兴起的五、六百年间,佛教各派普遍承认过去的六佛和未来的弥勒佛,但释迦牟尼始终被认为是唯一现存的佛。这种信仰本质上是与教主崇拜相联系的一佛信仰。大乘佛教兴起之初,在崇拜对象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在神化释迦牟尼基础上建立多佛同时并存的新的信仰体系。这不仅是所有大乘典籍和教派的共同主张,也是大乘区别于此前佛教的一个重要标志。大乘佛教在崇拜对象方面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与其基本教理、修行方式和整个学说体系发展演变密切相关的,值得深入考察。
大约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2、3世纪,相继产生的大乘各类佛教典籍数量十分庞大,包括般若类、华严类、大集类、涅槃类、唯识类、法华类等,它们都曾分别结合对基本教义的阐述,树立各自的信仰新对象,完成从释迦崇拜到多佛崇拜和新佛崇拜过渡的学说。对于从教主崇拜过渡到多佛崇拜的方式和途径、多佛的来源、存在依据、基本特点及其与释迦教主的关系等问题,各类大乘典籍的论述并不相同。总的说来,各类典籍中的佛崇拜学说既有与各自基本教义相联系的特点,又在传播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对这些典籍的学说进行全面、系统梳理,不仅可以深入探索大乘佛教有关佛崇拜的发展演变规律,也有利于从一个侧面更深入地理解大乘佛教思想和学说的形成历史。迄今为止,这仍然是学术界有待充分展开的研究工作。
本文不能对多种大乘经典的佛崇拜学说进行全面考察,只是通过对现存华严类译籍中的若干单行本和晋译《华严经》(指佛陀跋陀罗所译的60卷《大方广佛华严经》,以下也简称“集成本”)的比较研究,论述华严系统中佛信仰形成的具体过程、基本特点,以及与基本教义的联系,并由此揭示华严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与般若学的一些交涉和关联。
二、释迦分身
现存最早的华严类译籍是东汉末年支娄迦谶所译的《佛说兜沙经》(以下简称《兜沙经》),它明确列举“今现在”诸佛,宣扬多佛崇拜。本经宣扬多佛信仰的特点,是以释迦牟尼的“分身”来论证多佛存在,并且以此把释迦崇拜和多佛崇拜结合起来。在这部约2500字的小经末尾,描述了佛的世界和多佛并存的状态:
释迦文佛(即释迦牟尼佛),都所典主十方国,一一方各有一亿小国土,皆有一大海,一须弥山,上至三十三天。一小国土,如是所部,凡有十亿小国土,合为一佛刹,名为蔡呵祗。佛分身,悉遍至十亿小国土。一一小国土,皆有一佛。凡有十亿佛,皆与诸菩萨共坐十亿小国土。诸天人民,皆悉见佛。[1]
这里描述的释迦牟尼佛教化的整个世界,即“一佛刹”,是最早的华严世界构造,以后发展为莲华藏世界海。在“一佛刹”中,无数同时存在的佛都是释迦牟尼的“分身”。对于这种“分身”,本经没有进一步界说,但突出强调释迦牟尼佛身超越时空的遍在性,以此作为多佛并存的根据。这样,“释迦分身”说成为《兜沙经》把释迦教主崇拜与多佛崇拜结合起来的理论纽带。
从这种论述中可以看到,早期华严典籍倡导多佛崇拜的思路明显与般若类经典不同。同为东汉末年支娄迦谶翻译出的《般若道行品经》,就把多佛并存的根据放置在“般若”上:
过去当来今现在佛,皆从般若波罗蜜出生。
六波罗蜜者,佛不可尽经法之藏,过去当来今现在佛,皆从六波罗蜜出生。
十方今现在不可复计佛,悉从般若波罗蜜成就得佛。[2]
把多佛并存的原因归结为“般若”,使其具有成为诸佛之母的地位,凌驾于诸佛之上,自然贬抑了教主释迦牟尼的地位。般若类经典所要神化和抬高的是新兴教义“般若”或“经法之藏”,而不是某个人格化的大神。这样,般若类经典就不是用神话,而是用抬高佛教教义的办法解决多佛的来源问题。这种思路不仅具有强烈的批判偶像崇拜的精神,而且在树立新的信仰对象的同时,解决了修行者如何成佛的问题。这是释迦分身说所不具备的。
在大乘佛教之前,所有修行者无论怎样修行,无论修行多长时间,最高修行果位是所谓阿罗汉,而不是佛。佛只有释迦牟尼。既然承认多佛同时并存,就从理论上为信仰佛教的芸芸众生打开了成佛的通道。但是,要解决众生如何成佛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多佛从何而来的问题,在这方面,早期大乘经典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方案。《道行般若经》的论述,不仅解决了多佛并存的问题,也为众生成佛提供了可能的道路。因为,既然一切佛都是从般若波罗蜜中产生,那么,无论任何人,只要按照经典的记载修行六波罗蜜,就都有成佛的可能。换言之,凡按照佛教的新教义修行者,都理所当然的能够成佛。在早期的各类大乘佛教经典中,还没有这样明确的说明,但是,般若类经典已经有了这种趋势。
与般若类经典相比较,《兜沙经》着重树立释迦的权威,其多佛信仰的神话色彩更浓重,思辩色彩更淡薄,这不仅仅是两者在论证多佛并存方面的差别,也是两类经典在整体学说上的不同。《兜沙经》把倡导多佛与神化释迦牟尼联系起来,呈现出多佛崇拜与教主崇拜的天然联系,可以说是最早期的多佛信仰形态之一。同时,在这里的释迦佛已经不同于早期的“世间人”的形象,而是已经被神化者。很明显,华严系统中的多佛信仰是在神化释迦的基础上起步的,并且没有否定释迦作为教主和至上佛的地位。因此,仅就华严类典籍的范围而言,大乘佛教的多佛信仰学说一开始并没有对以前的佛教信仰予以全盘否定,而是依据基本教义的要求对崇拜对象进行了重新塑造。但是,与般若经典的同类思想相比,释迦分身说只解决了树立多佛信仰问题,没有接触众生如何经过修行而成佛的问题。所以,释迦分身说在后出的经典中被修正,论证多佛信仰的新理论也随之出现了。
三、十住兴佛
在早出的华严类经典中,我们只在东汉末年译出的文殊经典[3]中见到这种“释迦分身”说,在后出的华严类典籍中,无论是文殊经典还是普贤经典,都没有再继续强调这种早期的说法。三国时期支谦译出的《佛说菩萨本业经》(简称《本业经》),在继承《兜沙经》主要内容的同时,提出了新的多佛并存思想,即把多佛并存的根据放置在佛的教法上,也就是华严类经典提出的独特修行理论上。《本业经·十地品第三》在说明“十住”的重要性并予以总结时说:“一切十方去来现在佛,皆由此兴。”[4]按照《本业经》的说法,修行者从“发意”(树立佛教信仰)到“补处”(获得诸佛功德)的十个修行阶段,称作“十住”或“十地住”[5]。在此经中,“十住”是对整个佛教修行过程一个方面的总概括,它在本经中的地位,与“六波罗蜜”在般若类经典中的地位相似。把多佛并存的根据确定在“十住”上,与般若类典籍把多佛并存的根据确定在“六波罗蜜”上,归因于“经法之藏”上的思路是一致的,而与早先以释迦分身来论证多佛存在的思路完全相左。因为,“十住”乃是佛的教法,认为过去、未来和现在的诸佛由此而生,与把“般若”作为诸佛之母的说法没有本质区别。由于华严类典籍晚出于般若类经典,这种转变明显是受到了般若学的影响。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两种现象:其一,“十住兴佛”说与“释迦分身”说直接对立,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并存于同一类经典中,反映了早期同类大乘典籍思想起源的多元性。由于多佛来自“十住”的说法既解决了树立新的信仰对象问题,同时也对修行者如何成佛的问题有了说明,因此,较之释迦分身说有更大的适应性,并且有利于树立华严教义的崇高地位。所以,在后出的大量华严类典籍中对此进一步予以强调[6],成为占主流的思潮。相反,释迦分身说逐步失去了其重要性。
其二,《本业经》是直接从《兜沙经》扩展而来,都属于文殊经典,由此可以看到,华严类典籍在初期发展中就受到了般若类经典的影响。这就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早期各类大乘典籍在形成过程中,大约普遍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情况,都不是在彼此封闭、隔绝的环境中孤立发展起来的。
四、法身分身
西晋译出的华严类经典以普贤经典为主,这类经典论证多佛并存的依据是“法身分身”说,构成了华严经学论证多佛来源的第三种形态。
普贤经典进入华严典籍体系是晚于文殊经典的。与此前的文殊类经典相比,竺法护的普贤类译籍以法身为终极崇拜对象,贬抑了释迦牟尼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多佛的产生也发生了变化。多佛不是来源于释迦的“分身”,而是来自法身的“分身”。法身成为多佛的来源,成为多佛产生的依据。《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上称:“法身无量,而皆具足,名流显称,普至十方……皆能分身,十方现化。”[7]
在《兜沙经》中,同时并存的无数佛毫无例外是释迦牟尼的“分身”,在这里,“十方现化”的诸佛统统是“法身”的“分身”。这种着意的改造,表明后出的普贤经典要与前出的文殊经典在学说上保持一致的意图,从而给我们透露出华严类典籍形成过程的信息。同时,改造文殊经典中的学说,也与进一步改造和吸收般若学说以充实华严思想有关系。
所谓“法身”概念,最初来自对佛所说教法的人格化抽象,普遍被运用于各类大乘佛教经典。就般若类经典而言,对“法身”的界定、说明和发挥,与其倡导的“性空假有”的基本理论相适应。按照般若经典的一般看法,法身体现“性空”,没有可以为人们的感官把握的外在形象,只因为人们怀有“吾我”的错误观念,才把本质上虚幻不实在的幻身当作是实有的。如果消除以自我为实有的错误认识,幻身也就不会出现,也就取得了正确认识,可获得候补佛(阿惟颜)的资格[8]。因此,强调法身本质上的虚幻,强调取得般若智慧,是般若类经典论述法身的两个侧重点。然而,同为竺法护翻译的华严类经典,对法身的论述则不同。概括而言,强调的侧重点有三方面。
第一,法身是多佛产生和存在的本原、依据,永恒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佛说如来兴显经》(以下简称《兴显经》)卷1谓:“去来今佛,一切悉等,为一法身。”[9]把法身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佛的本原,作为诸佛之母,认定其永恒常存,是多种大乘经典的共同主张。华严经典则由此强调和论证多佛产生的根据。
第二,强调法身的遍在性,进一步论证法身是成佛的内在根据。《兴显经》卷2谓:
菩萨设若亲近如来,则为归道。所以者何?无所见者,为见如来。见如来者,则为一法身。以一法身,若一慈心向于一人,则为普及一切群萌,多所将养,如虚空界,无所不包,无所不入……佛身如是,普入一切群萌之类,悉入诸法[10]。
这里的“佛身”与“法身”的含义相同,这段论述首先明确了法身在佛教解脱论中的地位。法身可以“普入一切群萌之类”,从而使每个人都具有诸佛的本原,这是人人皆有佛性,皆有成佛内在根据的理论前提。把法身遍在延伸到人的心性方面,自然得出人心本净的结论。这也是华严类典籍强调的一个重要理论,竺法护所译的《渐备一切智德经》(以下简称《渐备经》)中有明文[11]。另外,法身可以“悉入诸法”,表明精神实体可以赋予无情之物,从而为泛神论的展开铺平了道路。
第三,强调法身的神通显示功能,即法身的“善权方便”。《度世品经》卷4说:
一切诸佛,合同体故,以得成就,弃捐一切诸凶危法,是谓法身善权方便,一切现门,神足变化,皆能显示。[12]
如来至真,其慧无限,随时说现,见诸自大,以权方便而发起之。法身无漏,悉无所有,普现诸身。[13]
所谓“善权方便”,在这里是指法身为了拯救众生从不可见到可见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法身转变为色身的过程。法身本来没有特定的可视形象,但它具有“普现诸身”、示现一切身的功能。在般若类经典中,法身从不可见到可见的原因被归结为人们的错误认识,华严经典与此相反,把这种转变归结为佛拯救众生的能动作用,这种转变并不以被拯救者的意志为转移。
法身的善权方便,集中体现在“神足变化”上。所谓“神足变化”即指神通,其本质特征是:通过对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如身眼耳心等)能力无限夸大的想象,以达到不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制约的随心所欲(“如意”)和绝对自由(“自在”)。神通的获得,被归结为修习禅定。《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卷中说:“一切变化境界,是皆定意。”[14]因此,法身的显示功能,来自对神通变化境界的构想。充斥于华严经典中的诸种神通构想和神话交织,在组织华严经学中起着重要作用。
既然法身显示出于拯救众生的需要,那么菩萨修行的终极目标,便是掌握这种功能。这既表明菩萨具备了诸佛的功能,也表明他具有拯救世人的无限能力。《度世品经》卷6有言:菩萨“察其世俗,缚在贪欲而缠绵,无能拔者……便以法身显示大要,遍于三世,令各生意”[15]。按照这样的思路展开的普贤类经典,为展示神异灵迹提供了最权威、最崇高的系统论辞,成为日后华严集成本的重要内容。另外,重视基于禅定特殊感受而引发的神通境界构想,强调神通变化在个人解脱和拯救众生过程中的作用,也为如何塑造修行的样版定下基调。这就是对普贤行和普贤境界的描述。
五、普贤境界
对普贤行和普贤境界的描述,集中在《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中。普贤菩萨的一个最显著的特性,就是可与法身相契合。佛告诉众菩萨:普贤“于三世等诸佛法身”,“等吾神足境界”。这样,普贤也就首先成为永恒的绝对精神存在,所谓普贤境界,佛的神通(神足)境界和法身,三者在这里就完全相同,没有区别了。
普贤之所以能与法身契合,达到与“法身等”的境界,在于他经历了与诸佛相同的修行过程。这个修行过程称为“普贤行”,也称之为“无限行”。所谓“无限行”,是强调其修行具体内容的多种多样,包罗万象,无穷无尽。这种无限行概括起来无外乎两个方面,即积累个人的无限功德和拯救无量众生。该经卷上借佛之口概括了普贤行:
普贤菩萨以净无数众生,无极清净,无量功德,兴无数福,修无数相,德备无限,行无等伦,名流无外,无得之行,普益三世。有佛名誉,普而流著。普贤菩萨,行绩若斯。[16]
在积累个人功德方面,普贤“兴无数福,修无数相”,经历了无数的修行实践,从而达到“有佛名誉”,实现了个人解脱成佛,这属于自度。在拯救众生方面,普贤“净无数众生”,这属于度他。自度和度他是同一修行过程的两个方面。
尽管普贤行具有无限性,但普贤能于法身契合的关键是神通行。于是,号召学习普贤,最终是鼓励修习禅定以获神通,此即为修普贤行。所谓“菩萨以几无思议之定,得应普贤之行”[17]。在此类经典中,没有修习禅定所获得的神通变化,与法身契合就是一句空话。
普贤能够与法身契合,也就是具有了法身的显示功能,为了让聚会的菩萨见到他,他又从不可见转变为可见,“普贤菩萨,兴为感动,使其大众,咸见普贤,于世尊足左右,坐大莲华上”[18]。这种变化,实际上也就是从法身到色身的转变。能够具有这种转变能力,也就与佛没有差别了。所以“普贤能化为佛,能住如佛,能化法轮,建立应化,普现如来之光明”[19]。这样,作为菩萨修行成佛样板的普贤,并不是以学问精湛、能言善辩、智慧超群见长,而是以具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变化、具有法身的善权方便著称。因此,从多佛的存在根据是法身,就开辟出了成佛的新途径;由于成佛的关键在于法身的“善权方便”,就决定了修行样板的特点。从这个方面把华严类典籍与般若类经典相比,可以看到前者的学说更重视神通、重视神异灵迹、重视偶像崇拜。
六、卢舍那佛
在华严类经典被系统整理、修改并编辑为集成本的过程中,它的佛崇拜体系又经历了最后一次变化,这就是晋译60卷《华严经》把卢舍那佛塑造为最高崇拜对象[20]。
卢舍那佛并非《华严经》首次提出,《杂阿含经》中已经有其名,《梵网经》中也有描述。但是,用它取代释迦牟尼的地位,使它既具有法身诸特性而又人格化,则是《华严经》的创造。
按照大乘佛教一般看法,作为佛的教理神格化的“法身”,是一种永恒而普遍的抽象存在,无形无相,不可名状。人们所接触到的佛,只能是其应化身,绝不是法身。在集成本出现之前的各种华严类单行本中,论述法身最多的是竺法护的普贤类译籍。它们对法身的界定和描述虽然与般若类经典不尽相同,但在区别法身与应化身或色身方面,坚持着大乘佛教的共同看法。集成本的佛身信仰有所改变,给此前普遍流行的法身概念赋予了新意。
对卢舍那佛的描述散见于全经各处,尤其以最初两品和最后一品的某些段落论述最为集中。各举一例,可见大体面貌:
佛身清净常寂然,普照十方诸世界,寂灭无相无照现,见佛身相如浮云。一切众生莫能测,如来法身禅境界。[21]
……卢舍那佛成正觉,放大光明照十方,诸毛孔出化身云,随众生器而开化,令得方便清净道。[22]
卢舍那佛不可思议清净色身,相好庄严,我见此已,起无量欢喜[23]
按《华严经》的描述,卢舍那佛是唯一的如来,真正的世尊,十方微尘数诸佛都聚集在他的周围,成了他的化身。诸佛、诸菩萨乃至诸善知识所表现的一切功德和智慧,包括他们演说的全部佛法,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他的神力赋予的结果。
作为最高崇拜对象,整部经典从头到尾,卢舍那佛没有说过一句话,他的存在从诸佛、诸菩萨的赞叹中及其各种活动中表现出来,加之他的身体“清净常寂然”、“寂灭无相无照现”等等,共同构成了他所具有的法身佛特性的一面。
卢舍那佛具有一切智慧和最高觉悟,接受众生的供养膜拜。同时,他也给自己的信仰者以智慧和觉悟,包括诸种神通,引导众生进入“方便清净道”,走上成佛之路。他的“相好庄严”的“清净色身”,他的“随众生器而开化”的“化身”,共同构成了他所具有的化身和报身佛的一面。
集成本的创新在于:集中把法身限定在卢舍那佛这样一个具体的佛身上,从而把“法身”和“化身”、“报身”统一起来,使其具有了三位一体的特性。这样,本来深奥难懂的“法身”被通俗化了,使需要费尽心力领会的玄妙佛理,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假思索即可敬奉的形象化实体。
“卢舍那”的梵文词含有“光明普照”的意思,也是太阳的别名。前出的华严类单行经也有佛发光普照佛刹的描述,但往往把佛发光与其身体的某个部位相联系,如足下、眉间等。这种情况也残留在集成本的许多品中。然而,集成本描述佛发光的核心内容,是把卢舍那佛描述为一个发光体,如同太阳。所谓“佛身一切诸毛孔,普放光明不可议,映蔽一切日光明,遍照十方靡不周”,[24]可以说,以卢舍那命名佛,是长期将佛比喻为照耀一切、生育一切的太阳的结果。这样,华严系统中的卢舍那佛就是光明的象征,它的光芒普照一切,使人们在佛光中获得智慧,并藉以实现自我净化。从华严类经典产生的地域来分析,以佛为太阳,不排除受到了祆教影响,受到了波斯文化影响的可能。同时,集成本还把佛光比作月光:“佛于诸法无障碍,犹如月光照一切”[25]。两种比喻穿插互见,有着以光明驱除黑暗的意义,这也是与祆教的教义相通的。
最为重要的是,佛发光之说,佛教有着自己的学说发展逻辑历程。大体言之,先有佛身某个部位发光的描述,逐渐演进到把佛描述为一个发光体。佛之所以能发光,最初源自他的智慧冥想,这一点也保留在集成本中。“卢舍那佛于念念中放法界等光,普照一切诸法界海。”[26]“法身”概念形成之后,发光之源又被安置在法身上,集成本也是这样论述的:“法王安住妙法堂,法身光明无不照。”[27]根据前面的引述,华严经典认为法身乃是“禅境界”。所以,法身之光、卢舍那佛之光的本原,正是来自佛“于念念中”的智慧的冥想实践,也就是来自禅定实践。简言之,佛光之说并不神秘,本质上是佛教僧人对禅定引发的特殊感受的发挥。把佛光比作日光或月光,大约吸收了外来宗教因素,但是,这并没有违背佛教学说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路线。就华严学说的主导方面而言,重视佛发光与重视禅定引发的对神通境界的构想有密切联系。这表明,《华严经》塑造新的崇拜对象,始终按照其基本教义的要求来处理。
注释:
[1]《兜沙经》,《大正藏》,卷10,449中。
[2]上引均见《大正藏》,卷8,469页。
[3]华严类典籍各品的内容与其主角菩萨有联系,“文殊经典”是指以文殊菩萨为主角的各品经。这是出现最早的华严类典籍。另一大类是以普贤菩萨为主角的各品经,称为“普贤经典”,其出现要晚于文殊经典。
[4]《大正藏》,卷10,450下。
[5]“十住”与“十地”在晋译《华严经》译出之前有混用现象,可以理出一条线索。三国吴支谦所译的《本业经》中有《十地品第三》,相当于晋译《华严经》的《十住品》,《十地品第三》中也讲“十住”或“十地住”。西晋时期,竺法护译《菩萨十地经》,《华严经传记》谓:“似《十地品》,《十住品》也”。竺法护所译的《渐备经》讲“十住”,相当于晋译华严经的《十地品》。东晋时期,鸠摩罗什上承竺法护,所译《十住经》即晋译《华严经》的《十地品》。晋译《华严经》是把此前经名中标“十地”的部分作《十住》,而把标为“十住”(是《本业经·十地品第三》内容的扩展)的作为《十地》。这是把后出的经典用了古称。
[6]竺法护所译的《渐备一切智德经》(简称《渐备经》)具有衔接文殊经典和普贤经典的性质。该经卷5指出:“十方诸佛,皆由(指十住)中兴”。并且认为:“行此十住”,就可以达到“自致成佛,度脱十方”。这些都是承自《本业经》的说法。晋译《华严经》中的《十地品第三》都有相关的内容。
[7][17]《大正藏》,卷10,575上、575下。
[8]竺法护所译《修行道地经》卷7《菩萨品》说:“法身无有形,用吾我人而现此身……法身无处,何缘得见?适思此已,便逮无所从生阿维颜”。
[9][10]《大正藏》,卷10,592下、598中。
[11]《渐备经》,卷1,“菩萨大士,以具大哀,不抱伤害,修本净心,益加精进,合集一切众德之本。”
[12][13][15]《大正藏》,卷10,637中、643上、651中。
[14][19]《大正藏》,卷10,584中、584下。
[16][18]《大正藏》,卷10,576中。
[20]把竺法护所译的《渐备经》、鸠摩罗什所译的《十住经》、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华严经·十地品》、菩提流支等所译的《十地经论》相对照,可以发现,后三个本子同为“卢舍那佛”的地方,《渐备经》为“如来至真”,未出现卢舍那佛名。这一方面表明,集成本的编定时间是在竺法护之后,另一方面也表明,对卢舍那佛进行全面塑造,使其贯穿于全经,是与集成本的整理、修改过程同步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推测卢舍那佛整体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但是它的定型不应该早于集成本的完成。所以,我们把树立卢舍那佛为最高崇拜对象作为集成本的创造,而不是作为华严典籍中某类经(或文殊或普贤等)的创造。
[21][25][27]《世间净眼品第一之一》,《大正藏》,卷9,399中、399中、399下。
[22]《卢舍那佛品第二之一》,《大正藏》,卷9,405下。
[23][26]《入法界品第三十四之十》,《大正藏》,卷9,736中、735中。
[24]《世间净眼品第一之二》,《大正藏》,卷9,403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