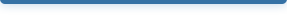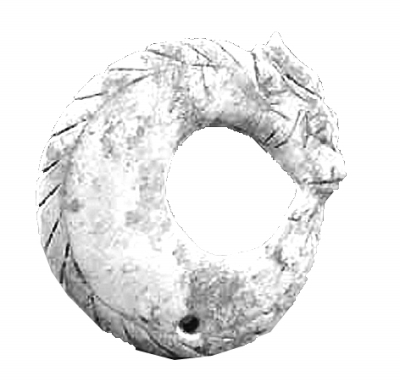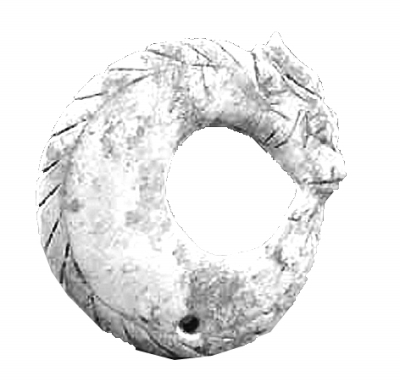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龙

大汶口遗址出土红陶兽形壶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人

牛河梁遗址出土女神头像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在《论中国文明起源》中精辟地指出:“谈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说,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提示我们在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中,不能只执着于什么是文明,也应关注什么是“中国”——这既包括关注中国文明之所以为“中国”文明的特色,也包括关注最早的可以称作“中国”的实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在中国文明探源研究中,应回答下面一系列关于“最初的中国”的问题: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共识最初是依据古史记载的五帝系统推算出来的,这些记载是后代的臆造还是有确实的根据?距今五千年之前是否初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可以以“中国”命名的文明?
⒈与生俱来的使命
中国现代考古学自1921年诞生之日起便开始了对上述问题的探索,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黄帝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观念得到广泛认同。依据古史记载推算,黄帝时代距今约5000年,因此出现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提法,并成为民国的有力文化依托。但正当此时,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提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的论断,传统古史系统面临严重威胁。众望所归,“科学地”重建古史成为中国考古学与生俱来的使命。
在当时的古史研究界,虽然古史辨派的“疑古”之风正盛,但新史学派精英们也开始吹起了强劲的“释古”之风,变单纯地破坏古史为以新资料、新视角释读古史。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蒙文通提出中国上古存在炎族、黄族和泰族“三系”;傅斯年提出了夷、夏二分说,等等。
以李济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在以考古学重建古史时,也是以“释古”为出发点、以古史记载为蓝图的。因为他们同样坚信:“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资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李济:《城子崖发掘报告·序》)
在得到由中国考古学家独立主持第一个田野项目的机会后,李济马上选择了晋南地区,因为那里正是文献记载的尧、舜和夏的活动中心。1949年以前,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以黄河中游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和以黄河下游为中心的龙山文化是仅有的两个被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因为傅斯年的重要影响力,考古学家接受了他提出的“夷夏东西”框架,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提炼出彩陶和黑陶两大内容宽泛的文化特征,将各地区主要的史前考古发现都纳入到这两大文化系统中,并以东西二元对立解释二者的关系。
上述开创性的工作对关于“最初中国”的问题做出了初步解答,认定古史记载是以史前文化的发展和互动为素材的,中国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这为后来的古史重建奠定了基础。
⒉从“中原中心”到“多元一体”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各地考古发现剧增。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已超过六七千处,文化类型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日益深入。新的资料表明,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二者并非同时并存、东西对立;而且,辽河流域,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各有自己的文化发展序列,再也不能用仰韶和龙山两大文化系统涵盖一切。夷夏东西模式失去效能,但其重视黄河流域的主旨得到继承,“黄河中心”模式或所谓“中原中心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当时的重要考古发现仍然多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多数学者仍然认为这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向周边地区传播先进文化因素,并孕育出最早的王朝。
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充分表明中原以外的史前文化区取得过毫不逊色的发展成就,在某些时期甚至处于领先地位。这对“中原中心论”提出了严重挑战。
严文明在1986年发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元性》,提出了折中的“重瓣花朵”模式。他指出,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很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有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如同第一重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如同第二重花瓣。此模式仍然强调中原文化区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但承认各地区相对独立的“花瓣”地位,承认各地区也有领先于中原的文明因素。但正如赵辉所指出的,中原中心地位的形成有一个过程,“重瓣花朵”未能准确描绘“最初的中国”形成时期的文化格局。
1981年,苏秉琦提出了著名的强调“多元一体”的“区系类型”模式,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有力挑战。他指出中国史前的多个主要文化区系沿各自的道路发展,均出现了“文明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中原只是其中的一颗明星。苏秉琦也明确提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任务之一是解决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他建立区系类型模式的用意正在于更好地描绘“最初的中国”。
几乎与此同时,张光直提出了他的“多元一体”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他将公元前4000年的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九个文化系统,指出,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各地史前文化互相分立,公元前5000年左右,新的文化出现,旧的文化不断扩张,“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放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我们也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既不设置中心,摆脱了“大一统”思想的束缚,又以考古资料可以清晰描述的区域间互动作为将各地区维系成“最初的中国”的纽带,为以考古学为基础重建中国的史前基础,解答本文开篇提出的关于“最初的中国”的那些重要问题提供了基本学术框架。
⒊“最初的中国”
由目前的资料看,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约在公元前3500年至3300年左右,也就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红山文化中晚期、崧泽文化中晚期和凌家滩遗存时期。该时期是中国史前史的灿烂转折期,各地区几乎同步上演着飞跃式的发展。
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出现大型墓葬,山东泰安大汶口墓地M2005的随葬品共计104件,包括陶器58件及石器、骨器、象牙器、獐牙、猪头骨和牛头骨等。在长江下游,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积石圈和大型墓葬,最新发掘出的07M23出土随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其中有长72厘米、重达88公斤的玉猪。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出现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圣地”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大型墓葬随葬大量玉器。在“中原地区”,河南灵宝铸鼎原周围的系统聚落调查显示,庙底沟时期的聚落数量和面积急剧增加,并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最大的北阳平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而小型遗址面积只有几万平方米。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各地区文化同步飞跃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明显加剧、新的社会上层闪亮登场的背景下,地区间的交流也有了质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远距离“社会上层交流网”的建立。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和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远隔1000余公里,陶器风格迥异,但玉器从形态到制作理念有惊人的相似,同样以龟、猪和鸟的写实或抽象的造型为载体,表达近似的原始宇宙观。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中随葬凌家滩风格的玉人,凌家滩最大的墓葬中则随葬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表示龟的抽象形态的“箍形器”。大口缸是另一种上层交流的重要物证。这种特殊的“大器”在豫西、山东和长江下游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大型墓葬中均有出土,各地出土的器物应是本地制作,但形态相似,摆放位置相似,反映了通过交流形成的、相似的社会上层葬仪。庙底沟风格彩陶纹样的广泛传播是此文化交流风潮最亮丽的标志,社会上层交流应是彩陶最重要的传播形式之一。这些可以通过考古资料辨识的只是当时交流内容的一小部分,实际发生的交流要远为广泛和深入。
建立社会上层交流网是世界各地前国家复杂社会流行的“统治策略”。考古资料确凿证明,在中国的史前社会,社会上层交流网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凌家滩大墓和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大墓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访。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为获得超越本地普通民众的知识和物品、巩固权力,完全可以不惧险阻,千里远行。在这一交流网中交流的是宇宙观、天文历法、沟通天地的手段、各种礼仪、各种巫术和特殊物品制作技术等当时最高级也最神秘的知识,是标志身份和权力的奢侈品,是象牙和玉料等珍稀原料。各地区在如此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中国相互作用圈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时代,而牛河梁、凌家滩、大汶口和西坡等墓地大墓的主人们就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们获得和维护权威、交通远方的传奇功业,很可能就是古史传说的重要素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