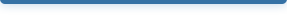余静远(外国文学研究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宏大叙事中,非洲大陆常常被边缘化,宛如一块被遗忘的拼图,隐藏在阴影之下。这片古老的大陆并非战争的旁观者,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他们为盟军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却在战后被西方中心论的叙事体系蓄意抹去。
西方的叙事偏见不仅剥夺了非洲的功绩,还延续了帝国主义的权力结构。我们要挖掘被遮蔽的历史,通过剖析当时非洲军团的实际贡献与文学作品中的战争回响,重塑非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位置。
非洲反法西斯战争的政治属性
战争是政治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将这场全球冲突置于20世纪全球政治发展的框架中,其军事行动背后清晰浮现出多重甚至相互矛盾的政治目标。对于德、意法西斯轴心国而言,战争是其极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治的暴力延伸;对于英、法等传统殖民帝国来说,它们抵抗法西斯侵略一方面是为了保卫本土和既有的全球霸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其殖民体系。而对于被卷入战火的非洲人民而言,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它既是一场反抗法西斯侵略的生存之战,也是一场抗击旧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独立之战。因此,从非洲视角出发,反法西斯战争的政治本质,是以民族解放为核心诉求,对全球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体系的一次总冲击。正是这一“双重属性”,构成非洲反法西斯贡献被西方历史叙事系统性边缘化的核心理由。
战后,西方大国为了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和残存的殖民利益,刻意在历史叙事中剥离这场战争的反殖民属性,将它简化为一场纯粹的、由西方主导的“自由”对抗“暴政”的斗争。这种叙事不仅导致非洲的巨大贡献被政治性遗忘,更从根本上割裂了反法西斯战争与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之间内在的政治连续性。
被“政治性遗忘”的非洲贡献
战后主流的反法西斯叙事,本质上是服务胜利者,特别是服务西方大国的政治利益建构。这种叙事建构是一种权力的延续,直接后果便是对非洲巨大贡献的政治性遗忘。
首先是对非洲贡献隐形化,核心目的在于维护殖民体系的合法性。二战中,超过100万非洲士兵被动员起来,在北非、东非、缅甸乃至欧洲本土为盟军作战。在艰苦卓绝的缅甸战役中,来自尼日利亚等地的英属非洲军团付出了惨重伤亡,其功绩却被笼统归于“英军”名下,其非洲身份也被刻意抹去。英国记者巴纳比·菲利普斯曾于2014年出版《他人的战争:缅甸男孩与英国遗忘的非洲军团》,书中提及为英国作战的“被遗忘的非洲军团”征战缅甸战场,揭示了这段被蓄意遗忘的历史。这类纠偏之作终究凤毛麟角。2022年,由美国迈阿密大学副教授埃德蒙·阿巴卡主编的论文集《非洲与二战:非洲的“被遗忘的”最辉煌时刻》从非洲视角重构二战历史,强调非洲的贡献——从军事参与到经济支撑——构成了盟军胜利的“最辉煌时刻”,却被西方叙事刻意遗忘,以服务于维持殖民遗产和全球霸权的政治需要。
其次是对非洲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消声,将战争简化为一场精英对决的“棋局”。西方主流叙事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偏见,即过度聚焦领袖决策和将帅韬略,而忽略非洲广大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为人熟知的“北非战役”叙事,往往聚焦于蒙哥马利与隆美尔的“猎狐者”与“沙漠之狐”对决——一场“白人绅士间的战争”。正如二战战地记者艾伦·摩尔黑德经典之作《沙漠战争:1940—1943年北非战役三部分》,其叙事焦点牢牢锁定在欧洲将帅的军事博弈上,而广大非洲士兵与当地民众则沦为这幅宏大“油画”中模糊不清的背景。这种对非洲人民群众的政治性遗忘,将他们描绘成被动承受战争命运的群体,剥夺了非洲人民的主体地位。
非洲文学影视作品中的
反法西斯叙事
非洲文学反法西斯叙事最深刻的理论贡献,在于挑战并重释了“反法西斯”这一概念本身。在欧洲中心的话语体系里,反法西斯是一场民主与极权、文明与野蛮的对决。非洲作家却敏锐地揭示了这场战争的巨大悖论:欧洲殖民国家在本土抗击法西斯的同时,却在殖民地维持与法西斯主义高度同构的统治体系。在非洲文学中,反法西斯的内涵被极大地拓宽了,指向一场更为持久和根本、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压迫、帝国主义和非人化统治的全球性斗争。
塞内加尔诗人列奥波尔德·塞达尔·桑戈尔的诗集《黑色的祭品》是非洲二战文学的丰碑之作。二战期间,桑戈尔作为“塞内加尔步兵团”的一员参战并被德军俘虏,诗集将这段经历转化为对殖民体系的批判:“我们中间最纯洁的战友已经死去,因为他们咽不下那种可耻的面包/现在,我们已沦为囚犯,受到文明人野蛮的虐待……我们曾经寻求过支持,但这种支持却象沙土上的塔一样倒塌/长官们,他们不在我们的身旁;战友们,他们认不出我们的模样/我们也认不出法兰西/我们在黑夜里大声呼救,却无人响应。”
另一位塞内加尔文学作家、导演乌斯曼·塞姆班通过电影,将非洲士兵的二战体验推向高潮。电影《第阿诺亚战场》基于1944年的真实历史事件,讲述了一群刚从欧洲战场归来的西非士兵,因要求得到与法国士兵同等的报酬和遣散费,竟在军营中遭到血腥屠杀。这一叙事无情地撕下了盟军“解放者”的面具,暴露了殖民体系在反法西斯口号下的残暴本质。尽管有少数历史学著作开始正视法国殖民地参战的作用、反思法国殖民帝国的道德性,但其主流叙事仍然围绕戴高乐将军在伦敦的号召,以及法国本土的“马基游击队”,以期塑造一幅法国依靠自身力量实现民族解放的英雄图景,刻意遮蔽非洲在自由法国运动中的关键作用。对于非洲人民而言,二战的结束并非解放的到来,而是让他们更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敌人不仅是法西斯,更是其背后的整个殖民压迫体系。战争的“胜利”并未带来平等,反而以血腥的方式激发了其彻底独立的决心。
与西非文学直面战争创伤的叙事不同,北非文学的杰出代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的《开罗三部曲》(包括《两宫间》《思慕宫》和《怡心园》),则通过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化为社会肌理的一部分,尝试精准捕捉战争作为一种“外部催化剂”,对本土社会结构的深层冲击与重组。小说以开罗中产阶级家庭阿卜杜勒·贾瓦德一家的代际冲突与演变为线索,跨越20世纪初至二战结束数十年,描绘了在英国军事占领下的埃及都市景观:战争虽未直接在埃及本土爆发,但其对埃及社会已产生巨大冲击,引发从传统父权制到现代民族主义转型的多重张力。在《思慕宫》中,马哈福兹生动刻画了年轻一代如何通过收听BBC广播、参与地下抗英活动,以及目睹盟军士兵在开罗街头的存在而逐步使民族意识觉醒;战争的“外部刺激”不仅加剧了家庭内部的代际断裂,还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独立诉求紧密交织,展现了民族主义情绪如何在全球战火的映照下日益高涨。这种叙事策略并非单纯的社会写实,而是对战争“双重属性”的文学诠释:表面上是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延伸,实质上却加速了埃及摆脱英国殖民控制、争取完全独立的政治进程。
东非文学则将反法西斯战争置于殖民暴力历史的连续谱系中,从而体现出深刻的历史穿透力。坦桑尼亚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小说《来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属东非为叙事起点,时间跨度涵盖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核心在于挑战西方以“战争/和平”为节点的断裂性历史观,代之以非洲视角下殖民暴力的连续性体验。小说聚焦“阿斯卡里”士兵——这些在一战中被德国殖民军队征召作战的非洲人,他们既是殖民体系的暴力工具,也是其受害者。主人公哈姆扎的战争创伤,无论是身体上的伤残还是精神上的屈辱,都成为一种无法痊愈的时代烙印,贯穿其战后的“来世”。对东非而言,德国殖民统治的结束并非解放的开始,而是无缝切换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因此,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再次笼罩这片土地时,对于经历过一战的非洲人而言,这并非一场全新的、关于“民主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不过是同一场帝国主义暴力的不同表现形式,是欧洲列强在非洲土地上争夺霸权的延续。“来世”这两个字本身就是点睛之笔,指涉的不仅是战争幸存者的余生,更是殖民创伤如何代际传递,如同幽灵般萦绕不散。在这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非具有独立意义的历史事件,而是被整合进一个更宏大的殖民历史叙事之中。要理解非洲的反法西斯叙事,就必须承认这场战争内嵌于一个长达数个世纪的殖民主义暴力历史的长河之中,其真正的“来世”影响至今仍在延续。
重构非洲的反法西斯叙事,不是简单的学术补白,而是对帝国主义遗产的批判。唯有真正承认非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才能构建一个真正包容的反法西斯记忆框架。在当代世界,面对新形式的霸权与遗忘,这种重构将成为推动全球正义的强大动力,让阴影里的褶皱和边缘化的声音重新定义历史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