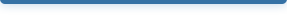每读《汉书·扬雄传》,常折服于扬雄波澜不惊的人生智慧。他以玄默淡泊的态度投身于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构筑完美自足的精神世界,在熠熠生辉的中华文明长河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人桓谭称誉扬雄“绝伦”都觉得还不够凝重概括,于是又称他是“西道孔子”外兼“东道孔子”(《新论》),意即天下人共同的“再生”孔子,从此奠定了扬雄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班固同样也很敬重扬雄,着意为他“设计”两卷的史传容量,悉数写录大赋四篇,西汉享此殊遇的文学家仅有他和司马相如两人,世称“扬马”,又坐实了扬雄一流辞赋家的文学史地位。扬雄曾游学精通老庄的严君平,思想底色中还透着道家的光辉,称得上是儒道兼济,即用道家的心态践行儒家君子风范,清心寡欲而又学行充盈。这一切构成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层面的扬雄遗产,或曰扬雄意义。
平心而论,面对两千多年前的贤哲扬雄,如何把握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和文化内涵,是重读古代名家经典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对其精神价值的提炼应当注重宏观与微观的辩证统一,兼融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和合之美。在宏观层面,提炼出“扬雄意义”的范畴,并就其内涵予以阐释,这无疑是理解和体认中华文明特质形态的一个侧面。同时也要在微观层面意识到,“扬雄意义”的生成是诸多细节的淬炼凝结,不应忽视细节在形塑意义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
蕴藉平和的讽谕风格
“扬雄意义”的内涵之一,是秉持“曲终奏雅”的赋学传统,而更趋含蓄委婉,甚至“没”其讽谕本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读四篇大赋,有时竟读不出扬雄的讽谏或劝谕“在何处”。
张震泽先生就此有精当的分析,他认为四赋“代表了自司马相如以后的新发展,也开拓了东汉大赋写作的新途径”,集中表现在“建立汉大赋的一种蕴藉风格”,可以称为“赋的蕴藉派的滥觞”(参见《扬雄集校注·前言》)。“蕴藉派滥觞”的提法,综括出扬雄四赋的创作新境及其独具的艺术魅力,体现了文学批评的历史尺度与审美尺度的统一。
回到四篇大赋的文本,第一篇是创作于元延二年(前11年)正月的《甘泉赋》,时扬雄年四十三,是出川入京的第二年。该赋的创作背景,本传有交代,称甘泉本是秦帝离宫,奢泰浮华,汉成帝每至甘泉郊祀,又常携赵昭仪随驾,仪仗盛大侈靡。显然,这都是扬雄创作该赋的讽谕对象。但如果本传不交代,单纯地读赋作本身,很难读出讽谕之意。比如,赋作写郊祀场面的宏大壮观,写宫殿堂宇的豪华奢丽,运用颇具抒情色彩的骚体句,“靡薜荔而为席兮,折琼枝以为芳。噏清云之流瑕兮,饮若木之露英”。多像屈原《离骚》的格调,真读不出讽谕在哪里。特别是这四句话:“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本传如不“提前”写出,“‘屏玉女,却虙妃’,以微戒齐肃之事”,能读出该段话是在讽谕成帝专宠赵飞燕吗?作为初入京师进呈成帝的首篇赋作,扬雄的讽谕力度实在太“柔弱”,诚如尚学峰先生所认为的:“讽谏意义也实在过于微弱,简直令人难以看出。”
扬雄在元延二年三月又创作了《河东赋》,据本传,成帝“眇然以思唐虞之风”,扬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罔”,遂作该赋。篇末“既发轫于平盈兮,谁谓路远而不能从”两句,写得委婉柔和,讽谕成帝不可因“路远”而怠惰以古圣贤为榜样,但若不是本传有所交代,同样读不出。
创作于同年十二月的《羽猎赋》,讽谕的“力度”较《甘泉赋》《河东赋》有明显的进步,篇末写道:“罕徂离宫,而辍游观,土事不饰,木功不彫,烝民乎农桑,劝之以弗迨”,“放雉菟,收罝罘,麋鹿刍荛与百姓共之”,“乃祗庄雍穆之徒,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遑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劝谏成帝勿耽于游猎郊祀等浮靡之事,应劝课农桑,而且进一步提出“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的主张。该赋奏进后,扬雄除为郎官,改变了待诏的身份。
元延三年,扬雄又创作了《长杨赋》,假托子墨客卿和翰林主人两人的对话,表达劝谏成帝勿沉迷畋猎、应胸怀万民之意。如借子墨客卿之口写道:“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霑而恩洽”,接着话题一转,称畋猎长杨的场面乃“此天下之穷览极观也”,发出“岂为民乎哉”的质问。讽谕的“力度”在四篇大赋里最强,可惜借助假托者之口说出,而且篇末又借翰林主人之口,否定了这种批评:“客徒爱胡人之获我禽兽,曾不知我亦已获是王侯。”子墨客卿也只好承认“大哉体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该赋的讽谕给人一种“虎头蛇尾”的感觉,像是刚伸出去的“脚”,又匆忙缩了回来。
纵观四篇大赋的讽谕功能,扬雄有直陈时弊的意愿,但总体上又是克制的,给人一种引而不发、发而又有所收的印象,可以窥探到他内心深处是谨慎持重的。扬雄的精神深处又交织着矛盾和纠结,以至于在他人生五十多岁之际反思赋的讽谏功能,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赋学批评观,认为赋“恐不免于劝”(《法言·吾子》),遂视己之赋作乃“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扬雄赋作讽谕追求的是雍容平和,直接导致其蕴藉风格的形成,而认定辞赋创作无法承担起真正的讽谕功能,则是蕴藉风格在文学批评层面的延伸。
儒道兼济的思想取向
“扬雄意义”的内涵之二,是儒道兼济的思想取向,既非完全的儒家有为入世,也非一味的道家自然无为,而是以道家心态践行儒家风范。
典型表现就是扬雄多次阐释“默”和“玄”,俨然将之视为两种哲学范畴。如《太玄经·玄摛》称:“故玄卓然示人远矣,旷然廓人大矣,渊然引人深矣,渺然绝人眇矣,嘿(默)而该之者玄也。”扬雄又称:“言不言,默而信也”(《太玄经·饰》),意即以不言为言,而达至儒家“信”的境界,不以言语为修饰则是道家的理念。此外还称:“无丧无得,往来默默”(《太玄经·守》),“闻贞增默,识内也”(《太玄经·增》),这都是扬雄以“默”为准绳的处世之道,正如黄侃所评价的“以容默处当世”(《法言义疏后序》)。
“默”是儒家强调的道德准则之一,如《论语·述而》称:“默而识之”,皇侃疏云“见事心识而口不言,谓之默识者也”。又《荀子·非相》称:“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辨不若其呐也。”“默”应与传统的儒家“仁义礼智信”并列。扬雄继承了“默”之智慧,又与“玄”结合在一起,进而提出“玄默”观。如《长杨赋》“以玄默为神”,又《解嘲》写道:“默默者存”“自守者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尤其是在《太玄赋》中,扬雄称:“我异于此,执太玄兮”,他不学屈原,不做伯夷、叔齐。“玄”还是一种人生哲学。我们习惯性认为,扬雄的“玄”,继承的是老子的思想,但若结合“玄默”来看,他的“玄”是对“默”的一种升华。“默”而深思,深思而致“玄”想,扩展到哲学层面是两种范畴,渗透到人生层面,则是为人处世的价值准则。
“玄”也离不开“默”。《汉书·扬雄传》同样强调“默”:“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深湛之思”也就是“玄”,实际是讲“默”与“玄”的辩证关系。扬雄面对成帝郊祀甘泉,非常纠结是否劝谏,本传说其“欲默则不能”而创作《甘泉赋》。时人以为《太玄》难懂,扬雄作《解难》写道:“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仍强调以“默”(“寂寞”)为主宰,致深思而达“玄”(《太玄》)境。《解嘲》说,“默然独守吾《太玄》”,以“默”支撑《太玄》的写作,“默”与“玄”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便友人刘歆认为,《太玄》恐怕覆酱瓿,扬雄也只是“笑而不应”,反映的仍是“默”的精神力量。
总而言之,扬雄的辞赋创作遵循委婉、柔弱的讽谕观,体现为蕴藉的风格特征,他在《长杨赋》里提出了“玄默”的观念,这种蕴藉可以说就是玄默观的一种体现。扬雄始终行走在讽谏的边缘,他不愿将辞赋创作与讽谏靠得太近,总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感。他创作《太玄》,意在构建其哲学体系,仍强调“默”的作用,“玄”以“默”为根基。扬雄无他嗜求,“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毕生都在遵循“默”之道。
扬雄为何这么执着于“默”呢?这或许与他口吃密切相关。《汉书·扬雄传》记载他“口吃不能剧谈”,《剧秦美新》又写道:“臣常有颠眴病,一旦先犬马填沟壑,所怀不章,长恨黄泉”,口吃恐怕也与他长期所患的颠眴病(一种中风类疾病)有关系。口吃使他不善言谈,遂自觉以“默”为人生追求和准则,把精力、精思和精华都萃聚在了文字上,留下了优秀的文学作品。“默”又使他深思,所以扬雄笃好“玄”理,“玄”是构筑哲学思维的重要方式,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著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