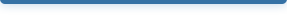2021年9月,著名批评家、后殖民文化研究奠基人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离开我们整整18年了。再次翻阅《东方主义》一书,使我又想起了与萨义德的交往。
1982年第一次到美国时,我就读过萨义德的一些文章,甚至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过,却不知他是巴勒斯坦人。以前我一直以为他是美国批评家,因为一般刊物介绍作者时,都只写他是“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系的帕尔教授”;直到1986年我认识他以后,才对他有了较多了解。
1986年秋天,在杜克大学举行的“第三世界文化的挑战”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萨义德。他衣着整洁,黑色的卷发,明亮的眼睛,显得帅气、聪明、干练。他热情坦诚地对我说:“我很想同你谈谈,可惜我马上要返冋纽约,你最好到纽约来,再忙我也要抽时间与你谈一次。”多么直率、热情!我仿佛觉得非到纽约去一次不可,于是我当即回答:“说定了,我一定去纽约看你。”
于是,会后我去了纽约,住在北大同学兰宜申家里。次日我给萨义德打了电话,按照约定的时间,1986年10月6日下午3点,我准时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汉密尔顿大楼他的办公室。室内除了一张硕大的办公桌和两把椅子之外,四周全是摆满图书的书架,门口附近墙上有块空着的地方挂着一副中文对联。
也许因为他的经历,也许因为我们已经见过,他对我非常坦诚,谈话中充满了友好和热情。当然,我们的谈话重点还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他首先向我谈了他对文学批评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看法。他认为,文学批评理论作为一次运动,其高潮已经过去。这次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出现在法国,其代表人物是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这样一些批评家。现在只有雅克·德里达还在继续发生作用。德里达虽然和他们源出一体,但他总是写些令人感兴趣的东西。萨义德说:“他们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多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虽然在美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我一直都不能完全赞同。”
萨义德认为,美国许多学者又在恢复传统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多的人对艺术作品本身给予更多的关注。但他认为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这就是在年轻一代学者中间,人们对文化研究更有兴趣。他说:“所谓文化研究,是指对文学、社会学和多种类型的艺术,根据其历史和社会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这种研究跨越了传统上不同的学术领域,颇受人们的重视。总的来说,纯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甚至解构主义也已基本结束。”“希利斯·米勒一直都在谈解构主义。但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拘泥于学院式的一些特殊的东西。”“你可以看看美国的情况,解构主义有哪些重要作品呢?德曼是个例外,但他已去世。哈佛大学的芭芭拉·约翰逊,人很聪明,曾是德曼的学生,可以说是最优秀的解构批评家之一。她写了不少文章,文章写得也很好,但很难说有什么创见,也不能说是重要的理论著作。”
萨义德是颇受美国学者推崇的教授和批评家,他博闻强识,著作甚丰。1976年,他的著作《开始:意图和方法》(Beginnings:Intention and Method)获得首届特里林纪念奖(为纪念批评家利奥奈尔·特里林而设的批评著作奖);1978年,他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批评著作奖的提名(因某些人的偏见被评为第二而未能得奖);后来他在1983年出版的《世界、文本和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获得了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以韦勒克命名的奖金。
但是,萨义德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困境中挣扎奋斗的结果。照他自己的话说,“我自幼失去了祖国,流落异乡他邦,不努力奋斗怎么行呢!”“我幼年时全家移居开罗,后来父母又移居黎巴嫩,此间还曾在欧洲国家短期流浪,这种环境使我自幼就养成了在困境中奋斗的性格。”萨义德1935年生于耶路撒冷,幼年在开罗上学,1951年到美国,先在马萨诸塞州的赫蒙山中学读书,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学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在各级学校中都是最优秀的学生。从1964年开始,他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任教。
然而萨义德并不是那种只顾个人名利而在异国求生存的学者。他富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充满了怀念故土的赤子之情。他用笔做武器,积极参与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他的《东方主义》和《巴勒斯坦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1979)从文化传统上分析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对宣传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曾被美国的极右势力视为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分子,遭到了抄家烧书的厄运。但他并未因此而畏惧、退缩,1986年,他又出版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该书不仅真实地描写了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的凄楚,而且呼吁巴勒斯坦人要充满希望,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集体的觉醒意识去争取巴勒斯坦人的团结和统一。萨义德为了便于与巴勒斯坦人民联系,为了保持强烈的民族情感,坚持留在纽约,谢绝了哈佛大学以优厚礼遇对他的聘请,他说:“我愿意留在纽约,因为纽约是个国际性的城市。如果我去了哈佛,我就会在那里买房子安定下来,就会与中东人的社区分开,这样我就会变成美国人了。”
萨义德的这种社会责任感,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同样得到反映。他常常从社会整体和文化语境来考虑问题,甚至连书名都明确指出这点,例如《文学与社会》《世界、文本和批评家》等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学术著作无一不贯穿着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他说:“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是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会有很大的差别。在我的故乡,在中东,一切文学都牢牢地与意识形态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尽管有程度上的区别,但无一能摆脱这种联系。你在讨论会上曾见到黎巴嫩的作家埃利亚斯·古里(Elias Khoury),他是我的朋友,他很想写些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的作品,但不可能,因为在那里一切事物都有意识形态的影响。我自己作为一个批评家,由于住在美国并同中东有密切联系,所以我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描述或解释文学作品与社会之间互相发生影响。我想这点是一定要了解的。”
萨义德认为,我们必须学会对事物富于敏感,对再现的东西,对研究的东西,对种族的思考,对不加批判地接受权威和权威的思想,对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作用,甚至对怀疑论的批评意识的价值认识,都要非常警觉和敏感。他说,“如果我们记着人文学科研究应有的道德意识——且不说政治意识——我们就不会不顾我们作为学者的责任,就不会不注意我们在做些什么。对学者来说,最高的原则就是人类的自由和知识。因此,对社会中的人的研究,必须以人类的历史和经验为基础,而不能以学院式的抽象为基础,也不能以晦涩难懂的规则或任意性的体系为基础;其目的是通过解释经验而提高人们的认识,促进人类的团结和进步。这就是我多年来在学术研究和著作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谈话结束以后,萨义德把我送到地铁站,反复解释他要开会,不能开车送我,也不能请我吃饭,仿佛他反倒对我有一种歉意。其实,对他那么热诚地同我谈话,把他的著作送给我,我心里早已充满了感激。这确实是一次难忘的有意义的交谈,它不仅使我对这位著名的批评家有了更多了解,加深了对他的作品和美国文学批评界的认识,而且他那种强烈的民族感和爱国心使我受到了很大触动。事后我确实想了很多,从文学想到社会,从文学批评想到爱国主义……
纽约晤谈时,他曾表示愿意来华访问,因此回国以后,我两次试图邀请他来华访问交流,但不知什么原因,都被他婉言谢绝。1991年冬天,我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从事两个月的研究,并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国际会议。萨义德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并举行了一次讲座,于是我们又见面了。他讲座的那天晚上,莫瑞·克里格做东,请萨义德吃饭,作为克里格的学生和萨义德的朋友,我也参加了那次晚宴。萨义德虽然风采依旧,但脸色显得不及以前,开始我以为五年不见了,可能是劳累或年龄的缘故,后来席间克里格和萨义德谈起他们的身体,我才知道他们二人患有同样的重病,都在靠药物维持。不言而喻,这是他谢绝来中国访问的原因。
2003年4月,我去杜克大学开会,然后去宾州州立大学访问,途中在纽约逗留了两天。其间我曾想去看看萨义德,但他的秘书告诉我他身体不好,不便安排,我只好作罢。不想那年9月24日,他便离开了人世。
一个伟大的学者,仅仅活了68岁,多么可惜!我现在只能缅怀他,并以此文作为对他的纪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