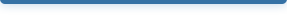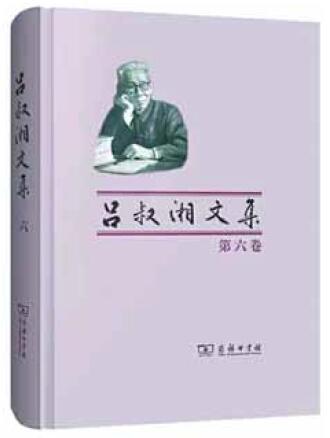吕叔湘(1904—1998),著名语言学家,江苏丹阳人。1904年12月生于江苏丹阳,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文系。曾在丹阳中学、苏州中学等校任教。1936年公费留学英国,入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系学习。1938年回国,任国立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后任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1950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主任。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1955年入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语文》主编、中国语言学会首任会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首任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名誉会长等。合编有《现代汉语词典》,著有《中国文法要略》《近代汉语指代词》《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教科书和著作,辑有《汉语语法论文集》《吕叔湘语文论集》《吕叔湘论语文教学》《吕叔湘文集》《吕叔湘全集》十九卷。

吕叔湘(1904—1998)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之一,他一生追求进步、胸怀理想,是一位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至高地位、极富社会责任感的学术大家。新中国成立时,吕叔湘在与夫人的一张合影背后题词:“青年人怀着远大的理想,老年人越活越年轻。——在祖国的土地上”。他就是这样,当时虽已人到中年,却仍以年轻的心态,把自己的学术理想寄托在新中国的土地上。
抱定文化救国的理想
吕叔湘的理想形成于年轻时期。五四运动爆发时,他15岁,在常州省立第五中学读书。五四新思潮强烈地冲击了少年吕叔湘的心灵。他在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在中学的末一学期,为了考哪个大学很伤了一阵脑筋。班上有好几个同学准备考交大(交通大学),也鼓动我考交大。父亲要我考政法专门学校,因为他吃过打官司的亏。我自己则想考文科,那时候很多青年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都准备献身文化工作。最后,我还是照自己的志愿报考东南大学的文理科。”
吕叔湘1904年出生在江苏丹阳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目睹了民生的贫弱和文化的凋敝。他就读的小学得风气之先,除了国学基础教育以外,还开设了国文、算术、修身、英文等“新式教育”课程,让年幼的吕叔湘产生了“文化救国”的理想。
在东南大学求学期间,吕叔湘如饥似渴地学习文理各门类的现代知识,新文化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他的心灵。直到耄耋之年,他仍不无自豪地对采访他的记者说:“直到现在,五四思潮还在我思想中起作用。”大学毕业后,他脚踏实地,在几所中学的教学实践中探索现代教学方式。之后不久,他获得了江苏省公费出国留学的资格。这个时候的吕叔湘已经不再是二十来岁的热血青年,工作实践也改变了他的思想,使他认识到民族复兴固然需要先进的思想,更需要切合实际的工作。193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到北平医学院从事整顿图书馆的工作,后又主持了苏州中学的图书馆管理工作。因此,他深知现代图书馆建设是推动文化教育至关重要的实际工作。就这样,为了学习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方法,他毅然决定把图书馆学作为自己留学的专业方向。那时,他的理想是学成归国后,从江苏省图书馆的改造和整顿入手,为民众的文化事业提供最切实的服务。
赴英留学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吕叔湘心忧故土,提前回国。为战事所迫,他辗转到了后方的云南和四川几所院校,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那些年,在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冒着日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吕叔湘顽强地做着学术研究。他心里想的是用自己掌握的现代语言学方法,解决一个又一个汉语历史悬案。而五四新思潮唤起的彻底改变全民文化落后面貌的宏大理想,彼时却苦于没有更合适的实现途径。
1941年3月的一天,吕叔湘的住处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时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的叶圣陶。叶圣陶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热爱进步,追求光明,长年致力于大众文化的普及和基础教育的改革。1940年他到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就任后,为推进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创意的举措,其中一项就是编写一本供中学语文教师用的汉语语法书。为此,叶圣陶亲赴华西协合大学吕叔湘的住处叩访。吕叔湘当时工作的研究所,主张“学术工作的理想是要专而又专、深而又深”。叶圣陶这次来访带来的理念——“语文教育工作意义不低于专业研究”,引起了吕叔湘强烈的共鸣。于是,他以极大热情投入这项工作,前后用了一年多时间,写出了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影响巨大的三卷本《中国文法要略》。

《中国文法要略》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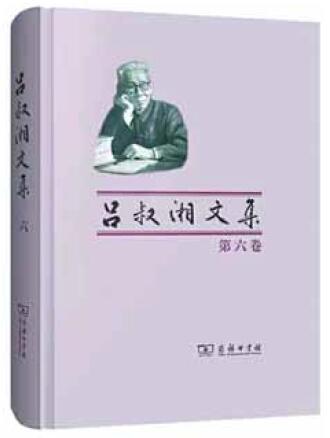
《吕叔湘文集》资料图片
从叶圣陶身上,吕叔湘仿佛看到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理想的光亮。从那以后,研究之余,他就跟随叶圣陶做语文普及工作。在叶圣陶主持的《中学生》和《国文杂志》等普及型刊物上,他撰写了大量关于语文知识、英语讲解、作文评改等方面的文章。1948年,吕叔湘举家迁居上海,正式加盟叶圣陶的开明书店。“开明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传为佳话,这种精神的塑造得自叶圣陶身体力行的倡导,也得自吕叔湘、朱自清等一批进步学者嘉言懿行的凝聚。他们以民众为本、以民族文化振兴为己任的精神,影响了中国几代学人。
1949年1月,叶圣陶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离开上海,从香港转道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吕叔湘和友人兴奋地为叶老送行,对新中国满怀憧憬。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吕叔湘在《开明少年》上的作文点评栏目里,对学生习作中表述的“我们可以不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得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了”甚为赞赏,因为这也寄托着他自己的心声。
现代汉语事业的奠基人
新中国的成立,让吕叔湘看到了民族文化复兴的曙光,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叶圣陶主导的新型教材编写和新型字典编纂的工作中。1951年,毛泽东亲自指示胡乔木找专家写通俗性的文章或教科书,对全社会进行普遍的语文知识教育。毛泽东对当时公文中较多存在的“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等问题很是警觉,同时也认为,党内良好文风的养成需要以准确的语法修辞知识为基础。在叶圣陶的举荐下,吕叔湘邀请朱德熙一同承担了这项任务。两人奋斗了三个月,写成《语法修辞讲话》,从6月6日起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郑重发表了由毛泽东亲笔修改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说:“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现思想,在今天,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每一个文件,每一个报告,每一种报纸,每一种出版物,都是为了向群众宣传真理、指示任务和方法而存在的。它们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因此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的力量。”吕叔湘和朱德熙合写的这部《语法修辞讲话》,有力地推动了语文知识的普及,在新中国文风建设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件事成为吕叔湘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他的工作与党的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自1953年底开始起草,至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吕叔湘从1954年3月就作为语文专家参与其中。3月初,宪法最初的草稿完成,董必武主持召开讨论会,邀请胡绳、叶圣陶和吕叔湘,用了三整天逐条推敲字句;3月下旬,中央正式提出了宪法初稿,起草委员会聘请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与其他专家一起,从不同角度讨论宪法草案、五个组织条例,以及刘少奇关于宪法起草的报告等各种文件。半年的工作异常繁忙,有时连续几天从早晨九点工作到晚上十二点。直至9月14日那天,又从上午十点工作到晚上七点,一直在中南海修改报告,吕叔湘记述道:“从三月初到九月中,今天是最后一次,功德圆满,少奇同志酌酒相劳而散。”次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讨论稿。吕叔湘和叶圣陶在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白话文的国家大法中,贯彻了他们自新文化运动就建立起的文体理念,倾注了对新中国民主政治的极大热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我国最高语言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吕叔湘不仅领导了新中国语言学的各项研究,而且全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部门所有重大的语文建设工作:确定现代汉语规范任务、拟定中学教学语法系统、研制汉语拼音方案等。
1955年10月,“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到会致辞,传达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的任务。《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说:“为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充分地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作用,以至为了有效地发展民族间和国际间的联系、团结工作,都必须使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明确,并且推广到全民族的范围。”吕叔湘在大会上宣读了罗常培与他合写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主题报告,强调“语言学家应该研究语言的规范,并且通过这种研究促进语言的规范化”。报告为此后若干年间我国的语言工作勾勒出蓝图。会后,国务院发出指示,责成语言研究所尽快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此后几年间,吕叔湘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中了。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以前的汉语辞书都是以文言为主的,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收普通话词汇、用普通话解释、举普通话例子的新型汉语辞书工作。“不但要学习近代的科学的词典编纂法,吸收先进经验,还要解决编纂汉语词典时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吕叔湘身先士卒,带领语言所的编写人员从各领域的文献资料里摘录规范词语和用例,上百万张卡片堆积如山。正式编写的那些日子,他每天准时到词典编辑室工作,中午常常只吃家里带来的馒头,晚上下班后,还把稿子带回家看到午夜,每周定稿工作量是1500多条,连周末也不休息。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吕叔湘带领词典编辑室完成了《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的编写工作,开创了我国辞书编辑出版的新时代,为我国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个人命运同党的命运相结合
1978年初,目睹了语文事业遭受到破坏的严重状况,吕叔湘痛切地感到,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基础,语文教育能否尽快走上正轨,对整个国家的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在1978年2月的一次座谈会上,吕叔湘就语言研究现状、中小学语文教学、大学公共外语、图书馆等问题做了专题发言。这个发言得到胡乔木的重视,将发言中有关中小学语文教学与大学公共外语的部分抄送邓小平。不久,这一部分内容以《当前语文教学中的两个迫切问题》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痛陈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十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大力主张各方面都要重视“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这篇文章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犹如一声惊雷,吹响了语文教育改革的号角。回忆吕叔湘晚年的学术工作时,他曾经的学术秘书张伯江回忆说:“年逾古稀的吕先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社会文化所受到的破坏而痛心,他认为尽快确立正确的中小学教育方针是重中之重。他四处奔走呼吁,强调中小学的语文教学问题;热心扶持语文教育中的新方法探索。八十年代初期那几年,吕叔相除研究性的学术会议以外,出席的最多的就是关于语文教学的种种座谈会;除研究性论文外,他发表的最多的也是讨论语文教学问题的文章。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吕叔湘希望用现代文化知识把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唤醒的话,晚年的吕叔湘更希望本来薄弱的社会文化水平尽快补回损失,实现社会文明的现代化。”吕叔湘认为,造成小学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是“学汉语”与“识汉字”的矛盾。“先识字、后读书、再作文”这种线型模式,使小学生入学后不能在原有的口语基础上及时地发展书面语言,不能达到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协调发展,延缓了小学生语言和思维的发展。1982年,黑龙江的几所小学做了三年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实验,吕叔湘对这一活动倾注了特别高的热情,多次听取实验进展汇报,并于1984年亲赴佳木斯参加教学实验工作汇报会,对这个实验给予大力支持。
吕叔湘一生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目睹了新中国给这个民族带来的复兴曙光。他在晚年时,曾对身边工作的年轻人说,他一生经历过的最好的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些年,二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吕叔湘与邓小平是同龄人,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相同的感受和愿景。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吕叔湘非常赞赏这个提法,他在多次讲话里,把语文教育改革的意义放到20世纪语文改革运动的背景下、放到“三个面向”的时代使命中加以论述。1985年元旦刚过,年过八旬的吕叔湘主动给《中国青年报》投去了一篇长文《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汉语和汉字的关系,讲了汉语汉字的演变和方言问题,介绍了白话文运动和汉语拼音化的前前后后。最后,文章联系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评论了汉语和汉字存在的种种问题。吕叔湘语重心长地说:“青年朋友们,未来是属于你们的。你们继承了一份语文遗产,它既有很多优点,也有不少缺点。怎么样发扬它的优点,克服它的缺点,就有赖于你们的努力了。”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对比,使吕叔湘对共产党的信任日益加深,在工作中,他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新中国的成就使他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他郑重提出了入党申请。1984年,语言研究所第一支部正式讨论通过了吕叔湘的申请,他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满足了自己近30年的夙愿。
吕叔湘早已把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当作党和国家事业的组成部分。20世纪40年代,他本来已经制定了个人的长期写作计划。当新中国的语言规范和教育事业需要他投入更多精力时,他毅然放弃了自己的研究计划,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语言教学与研究的学术组织和社会公益中。他说:古人所谓义利之辨,分析起来,“义”就代表集体的利益、长远的利益,“利”则代表个人的利益和眼前的利益。“当仁见义”是他的做人原则,也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崇高觉悟的体现。
作为知识界的杰出代表,他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吕叔湘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七届代表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1982年2月,共和国的宪法迎来最重要的一次修订,2月22日至3月11日吕叔湘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期间,全程参与了宪法的文字推敲和民事诉讼法等其他法律的讨论。他对宪法中教育地位的凸显给予高度评价,在发言中说:“跟以往的几部宪法比较,这次的宪法修改草案的优点很多。我只说其中的一点,就是强调了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这样强调教育?因为教育是一切事业的根本。事情要人做,人要会做事情就得学习,就得受教育。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就要有搞现代化的人才,要加强高等教育,这一点早就有了一致的认识。可是搞现代化不但要有高级人才,还要有具有一定文化的广大群众来配合,否则也会事倍功半进展缓慢。建设物质文明少不了教育,建设精神文明更少不了教育。一个人,如果愚昧无知,就会做蠢事;一个国家,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人民愚昧无知,就会处处出问题。”
有口皆碑的一代宗师
吕叔湘是中国语言学的一代宗师,他的学术成就有口皆碑;他又是学者中的道德典范,学风人品人人敬仰。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为吕叔湘颁授名誉博士学位时,对吕叔湘的赞词是:“英语世界中,英文之用字造句法度遇有争议,常以佛勒之意见为准则。在中文领域中,我们则惯于以吕叔湘先生之意见为依归。”然而,吕叔湘本人却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他总是把自己看成单位里的一名普通员工、青年同志的良师益友。语言研究所已故老所长刘坚曾回忆说:“吕先生担任语言所所长多年,治所有方。我觉得他在治所时,始终是把培养年轻人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做的。吕先生给我们办过英语学习班,亲自担任高级班的作品讲授。现在回想起来,这项工作简直是浪费他的时间。但是吕先生肯定不这么想,每堂课他都是正襟危坐,严肃认真到了听课的人谁也不敢稍稍走神儿的地步。”同事李临定回忆说:“有一次我去吕先生家,顺便问到吕先生最近在忙什么,吕先生说最近一个星期他在琢磨一位年轻人写的论文,给她重新拟订了一个提纲,让她去重写,写完后,他再看。吕先生说这话时,语气很随便,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殊不知当时吕先生的行政工作、研究工作都很繁重。吕先生就是这样经常抽出整段的时间,来帮助青年人的。”
吕叔湘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他却不肯领受国家给的学部委员津贴,主动退还;他为北京大学审读教材,北大送来审读费,他又上缴给了语言研究所财务室;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吕叔湘文集》,他把所得稿费全部捐给家乡丹阳的中学和小学。1983年,为了推进祖国语言研究的发展,鼓励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现状和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有成绩的中国青年学者,吕叔湘捐献出多年积蓄,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几年后,他又把荣获首届吴玉章奖特等奖的奖金转入青年语言学家奖金。吕叔湘这种高瞻远瞩、寄希望于未来、奖掖后学的崇高精神,赢得了学界广泛的尊重。如今,这个奖项已更名为“吕叔湘语言学奖”,30多年来,奖励和培养了一大批语言学领军人物和学术骨干,吕叔湘的学术精神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代代传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