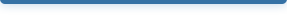公元前3000年左右至公元前332年是古埃及文明的法老王朝时期,埃及祭司马涅托(生活于约公元前3世纪上半期)将其划分为31个王朝。19世纪早期,普鲁士埃及学家列普修斯将31个王朝归入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个时期。之后,学者们在两个相对统一强盛的时期之间加入了“中间期”这一概念。古王国(约前2686—前2160年)与中王国(约前2055—前1650年)之间为第一中间期(约前2160—前2055年),两个政权几乎同时并立。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美国埃及学家D.B.斯班尼尔和B.贝尔为首的一批西方学者认为,第一中间期是古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个疾病期”或“黑暗时代”。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学者也基本持此观点。然而,20世纪末以来,随着考古证据大量增加,埃及学研究深入发展,这种观点越来越需要审慎看待。
构建为“黑暗时代”
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埃及学家主要依靠古埃及流传下来的一些文学作品和碑铭石刻理解第一中间期的历史。《涅菲尔提预言》写成于中王国时期,以预言的方式预测未来,该预言描述了社会饥馑和动乱:“埃及的河流空了,人(可以)徒步涉过……沙滩上没有水,河床上也没有水”,“大地上混乱无序”,“从来未发生过的事情发生了。人们拿起了武器,(因此)大地变得混乱。” 一些学者认为它反映的是第一中间期的社会状况。
《对美利卡拉王的教谕》是第一中间期的教谕文学作品。该文本讲道:“我以城市领主的身份兴起,我因为北方地区的情况而痛心疾首……我平定了整个西方土地,远达海岸”,“在我那个时代,一件可耻的事情发生了,提斯诺姆被洗劫了。”
上埃及希拉康坡里斯和埃德福诺姆的诺姆长安克提菲的墓铭文写道:“整个上埃及处于垂死饥饿状态,以至于所有人开始吃自己的孩子。但在这个诺姆,我设法确保每个人免于因饥饿而死。我把谷物借给上埃及……我使象岛的家庭活着。”阿西尤特诺姆的诺姆长凯悌二世在坟墓中记载了他的慈善行为:“我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礼物,我维持城市的生活,为中埃及山上的人们供水”,“我有很多谷物。我允许市民为自己拿走谷物,也允许他的妻子拿走食物,更允许寡妇和寡妇的儿子拿走谷物。”
正是基于这些文字史料的描述,现代学者对第一中间期形成了负面印象,认为当时整个埃及社会是病态的,并将这一时期称为“黑暗时代”。
王权呈现另一种面相
从古王国后期开始,诺姆长的职位开始在某个家族内部传递,从而出现了职位世袭的局面。到第一中间期,诺姆长的坟墓修建得异常庞大,墓室内部的壁画装饰、铭文和陪葬品几乎都是按照古王国时期国王墓葬的标准配备的。墓室铭文在记述墓主的功绩时,越来越少地提及国王的名字,而是更多地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这些情况表明,第一中间期缺乏强大的、能够统驭整个埃及的王权,地方诺姆俨然成为半自治的王国。
在第一中间期,下埃及和上埃及的几十个诺姆逐渐被整合到两个相对强大的政权中,一个是北方的赫拉克利奥坡里斯政权,另一个是南方的底比斯政权。前者被视作第9王朝和第10王朝(约前2160—前2025年)的政权,后者被视作第11王朝早期(约前2125—前2055年)的政权。这两个政权的统治者都自称国王,实施独立统治,管理着一些诺姆。阿西尤特地区的一个势力强大的诺姆长家族始终忠于赫拉克利奥坡里斯政权,与底比斯政权进行对抗。根据这个家族成员的墓室铭文,南北方的两个政权在后期展开了激烈战争。底比斯政权最终征服了北方政权,完成了统一上下埃及的“使命”。
单从统一国家王权的角度讲,与此前的古王国时期相比,第一中间期确实是政权分裂的时期。然而,这种王权统治的分裂是否必然意味着整个埃及社会处于混乱状态、经济文化呈现萧条与衰败局面呢?
并非处于全面长期动荡
如前所述,20世纪上半期及此前的很长时间内,由于涉及第一中间期的考古材料颇为缺乏,学者们主要根据一些悲观文学作品、教谕文学作品、墓铭传记等史料来描述第一中间期。其实,这些材料并非信史。
首先,悲观文学作品《涅菲尔提预言》没有交代所描述现象发生的具体年代,也没有说明事件发生的准确地点。从文本的语言特点来看,它是在中王国时期写就的。作者很可能为了凸显中王国社会的稳定,而故意夸大第一中间期某个时段、某个地方的混乱状态。因此,将《涅菲尔提预言》描述的社会状况视为第一中间期整个埃及社会的现实,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
其次,教谕文学《对美利卡拉王的教谕》是第10王朝老国王给新国王美利卡拉写的一篇说教文,核心是提醒新国王防范周围的人、保护好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国王。尽管教谕的叙述背景表明国王所在时代发生了战争,臣仆有谋害君主的行为,但教谕文学是以叙述者的个体经历来对新国王进行说教的,而且第10王朝只是第一中间期两个并列的政权之一。关于战争和人心不古的描写是否反映了第一中间期一百多年的社会状况,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埃及社会的实际情况,都是值得思考的。
最后,诺姆长安克提菲和凯悌二世的善行记录反映了一些社会现象,但这只是他们担任诺姆长期间所管理的诺姆的情况,而且关照弱者、伸张正义是高级贵族和诺姆长极力宣扬的,具有格式化的特征。这些表述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大,是值得深思的。
由此看来,这些史料不足以支撑“古埃及第一中间期整个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这一定论。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只能得出以下推论:在第一中间期的某个时间点上,埃及的某个或某些地方存在战争、混乱、饥馑等现象。
经济分散于地方
近些年,考古学家发现了第一中间期的一些墓葬和聚落遗址,这些考古成果反映出第一中间期埃及经济实力分散在各个诺姆。
首先,从墓地分布以及坟墓数量看,第一中间期埃及的经济收入大多留在地方,没有进入国王和王室手中。第一中间期,尼罗河西岸很多地方出现了墓地,这些墓地并没有以国王陵墓为核心,这说明当时国王的地位大大下降。第一中间期的墓地和坟墓数量比古王国时期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一中间期人口数量增加。坟墓数量增加,并且分散于各地,说明埃及人的经济收入有所增加,因为修建坟墓、制作棺椁和木乃伊需要很大成本。
其次,从坟墓形制和规模来看,第一中间期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古王国时期,国王陵墓庞大豪华,高级官员的坟墓往往建在金字塔周围,坟墓内部的装饰较少;所发现的平民坟墓很少,或许平民没有能力支付建造坟墓的费用。在第一中间期,国王几乎没有建筑金字塔,在中埃及的考姆·达拉发现的坟墓可能是第一中间期国王坟墓的一部分,而非金字塔残骸。第一中间期的国王墓以第11王朝国王荫太夫一世的坟墓为代表,位于底比斯(今卢克索市)尼罗河西岸的埃尔·塔利夫。其规模无法与金字塔建筑群相提并论,坟墓内部的结构和装饰也很简单。埃尔·塔利夫还有很多类似坟墓,可能是诺姆内部较小官僚和村庄居民的坟墓。中埃及的阿西尤特等地出土了很多诺姆长的坟墓,其规模与国王荫太夫一世的坟墓相似,内部装饰精美的浮雕和铭文,随葬大量物品。这表明诺姆长和其他地方官僚的经济实力增加,国王经济实力则大为削弱,这或许是诺姆长将资源留在诺姆内部的结果。
最后,诺姆首府城市周围有很多属于贵族的岩窟墓和马斯塔巴墓,还有大量城市居民的坟墓,埃及三角洲地区蒙蒂斯城的考古发掘表明了这点。城市居民的坟墓与村民的坟墓在形制上相似,但规模较大、陪葬品较多。这些墓葬表明在第一中间期城市有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表现。
文化表现形式有所变化
从考古发现看,与古王国相比,第一中间期的文化不再局限于主要宣传“王权神授”的国家意识形态,更多融入了广大社会成员的信仰和生活信息。
奥西里斯神是古埃及人崇拜的冥界之神,从第一中间期开始,阿拜多斯的奥西里斯神受到更多崇拜。该神庙或许早在第一中间期就已建立,普通人也可以到神庙祈祷献祭。这一时期,很多官员将自己的坟墓修建在阿拜多斯,距离较远的官员则在这里竖立石碑,希望来世获得奥西里斯神的庇佑。第一中间期和中王国时期的木棺及石碑上都有格式化的献祭文本,其核心内容是在阿拜多斯的奥西里斯神的认可下,把祭品给予死者的灵魂。
古王国时期,高官贵族的坟墓大多铭刻的是个人传记,例如大臣梅藤、乌尼、哈尔胡夫等人的传记,也有一些日常生活场面的描写。在第一中间期,诺姆长的坟墓有了新内容,他们不仅铭刻传记、绘制表现日常生活场面的墙画,还把家属和仆人的形象、名字及职业雕刻在坟墓内壁上;他们开始使用木制棺椁,并在棺椁上铭刻“棺文”。“棺文”的咒文大部分来自古王国时期国王使用的金字塔文,其目的是确保死者实现永生、在来世克服各种困难等。
第一中间期的墓葬出土大量陪葬品,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各种小雕像和模型。这些小雕像用木头、陶土、金属以及石头等材料制作而成,大小在几厘米至20厘米之间,形象各异、职业不同,其作用是在来世继续为死者服务。高官贵族的坟墓里有成百上千的小雕像,普通人的坟墓里也有几个或十几个小雕像。第一中间期第10王朝诺姆长塞赫麦悌墓中不仅有很多小雕像,还有两个战士模型,一个是努比亚战士模型,另一个是埃及战士模型。每个模型上有40个士兵,每10人一列,排成4行,诺姆长希望这些士兵来世跟随他继续战斗。这种小雕像和模型后来在中王国和新王国的坟墓中大量出现。
总之,在第一中间期,埃及处于分裂状态,没有统一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王权统治,存在两个政权相互征伐和外来入侵的现象,甚至有人民饥馑和社会不公的现实。然而,古埃及传统的王权制度依然存在;社会也不一定处于长达百年的全国性动荡不安中;各个诺姆的经济仍在发展,地方经济实力得到提升;文化领域更多地出现了民众的信仰和生活成分。这既体现了古埃及传统的延续,也为中王国时期埃及社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单纯依靠一些文学作品和传记铭文,就将第一中间期定性为“黑暗时代”,并不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