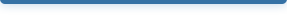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核心提示】在帝国主义时代,大国之间的妥协交易一向不在意被交易的弱国利益。美国为了扩大对中国的影响力,才对中国作出承诺。中国的职业外交家们被美国的表面承诺所迷惑,而无法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希图“以夷治夷”,最后却被大国出卖。巴黎和会上中国过分相信美国,希望借助美国来压制日本,结果只能是失败。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也是巴黎和会召开95周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也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个别学者借助新发现的外交档案,宣称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没有失败,认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观点是民族主义书写历史的产物,是政治宣传和神话。历史果真如此吗?本人特写此文反对这种观点,并坚决反对一些学者利用新发现的档案、日记等史料,以还原历史真相的名义,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以学术创新相标榜,颠覆基本历史结论的做法与企图。
巴黎和会的实质是帝国主义分赃会议
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国家安排战后世界秩序的会议,实质是一次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通过大量的资料和严密的学术分析,证明这场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他明确界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为:“当前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基本性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崛起的帝国主义与老牌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达到自己的最高形式,输出的已经不是商品,而是资本了。资本主义在本国范围内已经容纳不下,所以现在便来争夺地球上剩下的最后一些未被占据的地盘”,“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914—1917年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正是这样的战争”。孙中山也认为“欧战本为利害之争”。
巴黎和会是根据各国在战争中的“贡献”来决定这个会议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因此,决定会议的是英、法、美、意、日等国组成的五国会议。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向外交部汇报说,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在会议发言时,“雄辩滔滔,词锋犀利。玩其语意,一若此次和会,除美、英、法、义(意)、日五国外,余国之被邀入会,已属好意,直无可以商量之余地。其气概咄咄逼人”。陆徵祥已经感觉到“法总理如此态度,前途可虑”。这表明,巴黎和会是列强分赃的会议,根本不是弱国、小国争取自身权益的载体。
中国最初连参加和会的资格都没有,后来在美国的支持下,勉强被允许参加,但处处被看不起,根本不能指望列强同意中国提出的诸多条件。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是虚幻的,列强从未将中国视为平等一员,美国的“赞助”也不过是口惠而实不至。美国为了自己利益考虑,食言自肥,改变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中第一条“反对秘密条约”,即原定对中国山东问题的支持态度。
中国职业外交家们在与帝国主义打交道的过程中,也逐步认识到列强外交的实质。1915年9月21日,外交部参事夏诒霆在致北京政府的电文中,就提出“有强权无公理”。1917年4月6日,驻美公使顾维钧致段祺瑞电说:“日本经国大政,在谋操纵中国,欧战实其千载良机。”1919年4月7日,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在致北京政府的电文中坦言:“国际对我情形,今日更殊畴曩,列席人数,其尤著者也。即如我国全权到时,接待应酬之淡漠,列强领袖在会访问接洽之艰难,各界人物对华议论观察之轻慢,种种情况,江河日下。关于我国山东问题,除某国(美国)善意维持外,各国要人对我态度虽无不表示同情,然每以种种事实之关系,口吻多欲吐而仍茹。总之,强权利己之见,绝非公理正义所能摇,故协群力以进行,犹恐九鼎之难举。”
巴黎和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作为弱国、半殖民地国家,不可能通过它达到自己的目的。日本借对德宣战之名侵入中国山东,造成强占山东的事实,又利用北洋政府的私心,强迫、引诱之签订“条约”,获得所谓“法理”依据,还与列强相勾结,获得列强的认可。早在巴黎和会前,日本就与英、法等国协商,得到他们战后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保证。日本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强权的表现。在帝国主义时代,大国之间的妥协交易一向不在意被交易的弱国利益。美国为了扩大对中国的影响力,才对中国作出承诺。中国的职业外交家们被美国的表面承诺所迷惑,而无法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希图“以夷治夷”,最后却被大国出卖。巴黎和会上中国过分相信美国,希望借助美国来压制日本,结果只能是失败。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没有达到主要目的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主要目的就是收回山东权益。日本全权代表的使命是:“要求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权益及财产,并领有德国占领的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因此,山东问题成为判断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与否的主要标准。
中国最初以为收回山东权益是作为战胜国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在参加巴黎和会以后,由于日本执意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如何争取收回山东权益,就成为中国代表团的首要任务。代表团认为“目前山东问题最为吃紧,故所提问题即以此为限。深恐各项问题如果同时提出,不免使欧美各国转因自己的利益偏向于彼,在我反有孤立之势”。对中国代表团力争的山东问题,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三国会议决定:德国将山东的所有权益让于日本,日本将德国租借地及其他政治性权利交还中国,但保留经济性权利。由于日本反对,最后的条约文本只写明德国将其让与日本,而“于交还中国一层不提一字”。
当时,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就山东问题致电北京政府:“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直(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固,关系至巨。祥等所以始终不敢放松者,固欲使此问题留一线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之可言。”对于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最后决定,即使对外态度最为温和者,也不能不认为这是中国外交交涉的失败。
对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这个基本事实,有学者以所谓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口头承诺将把山东交还中国,列强也进行保证,这个口头承诺为华盛顿会议解决山东问题打下基础为理由,认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没有失败。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日本的承诺没有公开,也没有写入和约等公开文件,这在外交上并不算数。因为未公开,所以对时局也没有发生影响。从历史来看,日本的承诺从未兑现,历史证明日本从来没有停止侵略中国。华盛顿会议上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谈判,也并不是以日本的口头承诺为基础,而是与巴黎和会后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国内政局变化有关,更何况华盛顿会议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山东问题。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北伐经过山东时,仍然遭到日本的武装干涉,就是例证。不能拿这个所谓的承诺来否认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没有失败。即使有这个承诺,也不过是一种外交托词。帝国主义的承诺何其多。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不是也对中国承诺过吗?最后却出尔反尔。有学者仅凭外交档案中记载的日本口头承诺,就认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没有失败,未免太幼稚了。
我们认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并不否认取得的其他外交成果,也不否认职业外交官维护国家权益的努力。但是,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孤立地研究职业外交官的行为,并夸大其作用,忽视实际起支配作用的军阀,这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1915年5月,一些职业外交官在袁世凯政府的授意下,与日本签订《民四条约》,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原有权利。1918年9月,在皖系军阀的授意下,为了获得日本的借款而草率签订的《关于处理山东省各问题换文》,使日本在山东侵占的权益有了所谓“法理依据”,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交涉山东权益留下了无穷后患,外国人均认为此“授日本以口实”,“中国弱点惟在此”。五四运动将这些主事者称为“卖国贼”,当然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当年决定签署条约的军阀,更是民族权益的出卖者,不管以什么理由,也难以否认他们出卖民族尊严和国家权益的责任。
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富强,在帝国主义强权逻辑下,即使职业外交官们的外交技巧再娴熟,再精通国际关系,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弱国无外交、任人宰割的命运。中国代表团成员伍朝枢在总结巴黎和会时说:“二十世纪之世界,生存竞争之世界也。公理强权互为表里,外交内政息息相关。此次吾国外交失败原因,一言蔽之,国势积弱而已。或者不察以为列强主持公理,自可仗义执言,不知倚赖性根,最为我国民之弱点。”
须充分肯定五四运动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发端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那种认为中国外交没有失败的看法,实际上否定了五四运动的必要性和进步性。唐启华认为五四运动是“舆论喧哗与政客扭曲”的结果,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论是民族主义书写的产物,是革命史观与民族主义的政治宣传与神话。这种观点实际上借重新诠释“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问题,进而动摇五四运动的起因,否定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攻击、消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革命史观和民族史观,从源头上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
五四运动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民族压迫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唤醒了世界民众,也唤醒了中国人民,使帝国主义不能再随意决定世界人民的命运。列宁指出:“英德两个金融强盗集团争夺赃物的战争留下的几千万尸体和残废者,以及上述这两个‘和约’,空前迅速地唤醒了千百万受资产阶级压迫、蹂躏、欺骗、愚弄的民众。于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正是因为巴黎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使位居“战胜国”行列的中国蒙受战败国般的屈辱,激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烈愤慨和对当政者投机、软弱的强烈不满,导致五四运动的发生。把五四运动说成是少数政客煽动民众民族情绪的产物,是无知妄说,是对五四先驱们的亵渎。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不容否定。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反映了中国人民理性民族主义的觉醒,是对帝国主义强权的抗议,是对军阀控制的政府软弱无能的抗议,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维护,是对中国民族尊严的维护。五四运动迫使北京政府最终不敢下令签字,激扬了中国代表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书写了崭新的一页,标志着帝国主义从此以后再也不能无视中国人民的呼声。
1918年,梁启超说过:“现在世界之新潮流,曰国民外交。所谓国民外交者,非多数国民自办外交之谓也,乃一国外交方针,必以国民利害为前提也……当此国民外交时代,凡事之行,固在政府,而所以监督政府者,则在国民审查内外形势,造成健全之舆论,以为政府后盾。”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正是顺应了民众的爱国要求,是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而不是被民族情绪裹挟的反映。代表团成员顾维钧认为中国拒绝签字“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观点来看,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评价五四运动:“从巴黎和会的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一种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学生们正在为祖国的自由和复兴而奋斗的目的和思想,没有一个人会不表示同情”。参加巴黎和会的日本代表牧野伸显认为:“世人不察,以为在巴黎之中国委员,为血气所驱使,为功名所激发,致有此等行动。而余观察则不如是。余深信此种感情早已浸润于中国一般国民,酝酿已数年之久,有触即发,巴黎和会不过其表现之机会耳……此次中国委员既非激于意气,出于偏爱,而为代表国民全体之活动,则留意中日根本关系而欲图永久亲善者,又乌可漠然视之乎?我国或因中国问题而陷入意外之难境,未可知也。”
五四运动代表着中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这种觉醒,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当然结果,也是列强长期压迫中国的必然反映。五四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近代中国由不断丧失国家独立主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沉沦,而向着实现完全的国家独立、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上升趋势的转折点。
对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积极作用要充分肯定。近代资本主义的扩张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进步思潮,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产物,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对内要求各民族平等、对外要求与世界其他民族平等。在近代中国接踵而来的外患之中,民族主义发挥了凝聚民心、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作用。不能将个别的、非理性的民族情绪归结为民族主义。正是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才引起了中华民族的反抗。正如列宁所说:“一切民族压迫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遭受民族压迫的居民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依靠民族主义,通过民族战争,中国人民成功地推翻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压迫,取得了民族独立。列宁曾经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能性很大,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
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民族压迫和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干。按照民族史观书写近代中国历史,是符合中国近代历史事实的,根本不是政治宣传和神话,不但没有束缚国人的观念,反而能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个别人借口今天中国现实的需要,提出超越悲情民族主义,脱去“民族主义的硬壳”,重新改写中国近代史,这不但遮蔽了近代中国历史真相,反而会消损民族精神,从而严重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肯定中国职业外交家在通过外交途径维护国家主权的同时,要高度肯定革命在改变近代中国外交中的根本作用。中国命运的改变,不是靠列强的“善意”,而是靠国人的抗争,靠革命。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认为:国民不能单纯依靠公理的觉悟,不能靠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而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即以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正是高涨的群众运动,才使得近代中国的“修约”与“废约”融合,兼具法理依据与革命精神。1928年初,就有人指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最正当方法,当溶合二者而用之,即依法律手续而以革命精神行之是也。近来我国对外策略,殆已采用此项方法,如废除比、西诸约,一面以法律手续进行交涉;一面取决然态度,势在必行,无法律之手续,则不得国际之同情;无革命之精神,则不得最后之胜利。二者相并而行,然后事乃有济,此乃对外政策之所以比较成功也。”
日本学者川岛真认为,“依据中国的外交档案,重视当时时代和当事人的性质,就有可能忽视‘列强’的侵略而过度强调内在性质。尽管过去那些‘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侵略’之类的历史叙事的确存在许多问题,但从清末到民国,中国主权受到侵害的事实及其影响之大却是决不容忽视的”。
对此,必须高度警惕一些学者根据一些表象材料就否定一些基本历史共识。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要把近代中国若干重大事件的真相及体现出的历史规律告诉世人,告诉青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