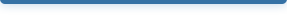编者按:伴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主题的变迁,对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不同判断和研究主体的现实政治诉求,形成了主导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研究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可以说,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史,就是“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萌生、形成、发展的演变史。本文作者以“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为中心,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做了深入的分析。
1、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
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学术界通称为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翻身、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说,也是中国由被动到主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中国向何处去”是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旋律。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先现代化,还是先革命,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考察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作为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继承了传统中国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传统——“资治”。从其一开始产生,就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学术,而且深受现实中国政治语境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被纳入现实主流意识形态中,为现实的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依据。在民族、阶级斗争紧张、激烈的时代里,近代史研究者集学者和政治代理人两任于一身,将学术研究当作救国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借中国近代史研究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构筑的近代史研究范式,折射了当时中国政治主题;他们的政治理念,深深地渗透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文本中。
反映不同时代政治主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因为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而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地位: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为国民党统治服务的以现代化范式为框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居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主流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以革命史范式为架构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居于学术边缘地位,构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由于政权变更,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的以革命史范式为架构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主流,从学术边缘走向中心,获得巨大的发展。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以现代化范式为框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中国大陆无容身之地,被遗忘了几十年;“文革”十年,为“四人帮”服务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近代史研究把革命史范式推向极端,成为唯一的“学派”,被改造为他们所需要的“体系”;20世纪80—90年代,由于“现代化”成为中国的政治主题,以革命史范式为架构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而以现代化范式为框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为学术的关注焦点。因此,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不仅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而且常被纳入各时期政治框架中。为政治服务,是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传统之一。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史研究极易受到政治的干预,这在十年“文革”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所以,正是在20世纪中国政治的强大推动下,在对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考察中,形成了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近代史研究;正是伴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主题的变迁,基于对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不同判断和研究主体的现实政治诉求,形成了主导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种研究范式——“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可以说,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史,就是“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萌生、形成、发展的演变史,也是二者互相竞争的历史。本文就以“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演变为主线,考察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及其启示。
2、梁启超是“现代化范式”萌生时期的代表
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科分支形成的萌芽阶段,是“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萌生时期。20世纪初西方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输入,为20世纪最早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考察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的思想武器。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范式”萌生时期的代表。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成为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现代化范式”的开端。因为“现代化理论是乐观的社会进化论思潮的产物。”指导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史观是进化史观,他认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
梁启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目的是为了现实服务,指导他考察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进化论,一开始就是与维新派变法图强的政治要求分不开的。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总体认识,集中反映在他为了纪念《申报》创刊五十周年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在该文中,他从社会进化的角度勾勒了近代中国演变的大致轮廓。他分别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一,“中华民族之扩大”。第二,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变。他认为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一直到甲午战争,因此掀起了学习“西技”的运动。第二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时间是“从甲午战役起直到民国六年、七年间止”。第三期,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三,政治进化。梁启超认为,“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所以五十年的中国,“最进化的便是政治”。
梁启超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对近代中国的总体认识,对于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实际上以社会进化为中心,为近代中国通史勾勒了一个大纲,是梁启超认为“通史最能体现社会人类进化发展的‘公理’和‘公例’”的学术思想在观察近代中国时的具体实践。
1901年9月李鸿章死后,梁启超11月立即就撰写了《中国四十年大事记》(一名《李鸿章》)。该书可以说是20世纪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比较严谨的第一部人物传记,是梁启超以新观点、新体裁、新文体相结合的第一部史学专著。梁启超写作此书时,抱“作史必当公平之心行之”的态度,也是以新史学理论方法著史的尝试。梁启超的《李鸿章》可算得上20世纪第一本中国近代史著作。1901年,《李鸿章》的出版,可视为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端。
梁启超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观点,体现了他的史学思想。梁启超虽然没有写一本中国近代通史的著作,但他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近代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观点,如他提出以“国民史”代替“二十四史”的“帝王将相家谱”;他认为过去“正史”的作用是为统治者统治臣民提供借鉴;为专制帝王培养忠顺臣民,对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很大影响。
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对清代学术与近百年学术史的研究,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探幽开微的功力,都为学术界所公认,为近代史的研究,建立了可信赖和足为信史的一些楷模。”梁启超将近代社会变革分为三个时期的论点,后来被香港学者金耀基在《从传统到现代》(1966年)一书中发展为现代化三层次说:甲、器物技能层次的现代化;乙、制度层次的现代化;丙、思想行为层次的现代化。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学术界又提出把晚清现代化分为三个运动的观点。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梁启超是20世纪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的第一人,也是20世纪从现代化视角考察近代中国的缘起。
3.李大钊、华岗是“革命史范式”萌芽期的代表
“五四运动”前后,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这一段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酝酿期。李大钊、华岗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萌芽期的代表。
李大钊不仅是20世纪宣传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是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人。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任务,李大钊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权力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为后者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 李大钊说他“数年研究的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今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缚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基于上述分析,他说“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重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所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
关于近代中国的基本线索,李大钊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位置》提出:由一八四一年,广东三元里乡民因愤英人携战胜的余威,由我偿军费六百万元,割香港,集众数万,奋起平英团。一八四二年粤人听到英迫我缔结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港口通商,割香港,留下协商关税的根萌的消息,聚众数万,反抗英人,焚其商馆 。一八四五年粤民举办团练,抗拒英人复入广州。一八四九年,粤人集众团十余万于河干,拒禁英人入广州城。中经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三合会,哥老会覆清仇洋的运动,乃至白莲教支流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运动,强学会,保国会、立宪运动、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一直到由“五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
李大钊对近代中国的基本线索的概括同后来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有非常相近之处,只不过毛泽东更强调中国的反帝反封的双重使命,李大钊强调中国历史是一部“民族革命史”。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李大钊对中国近代史还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只是一种观察和认识。但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阐释,却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他运用唯物史观对近代中国的初步认识,为后来马克思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提供了初步的理论观点雏形。
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工作者就是在李大钊开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道路基础上,开始中国近代史研究起步的,华岗就是其中之一。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初步地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
以李大钊、华岗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从现实民族革命的需要出发,是为了认识现实中国的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因此,从他们主观动机来说,他们并没有学科体系建构意识。作为革命者,现实也不容许他们从从容容地从事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初步认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中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看法,从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看,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早期的一个环节。他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观点,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认识基础。以他们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构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酝酿期。
1901—1931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由于当代人写当代史,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和现实性。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处在萌芽时期,学术水准一般不高。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只能算作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萌芽期。但从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学科发展史上看,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还是非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从指导思想、研究取向、研究方法、基本认识,等等,在一定程度上,都为后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奠定了初步基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史党建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