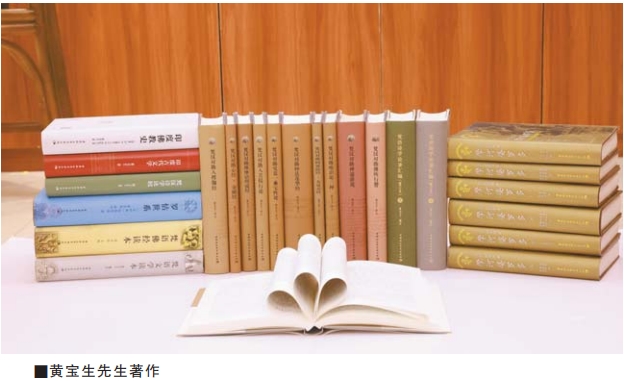在中印文明交流史中,梵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印度学和佛教学专家黄宝生曾在《梵学论集》代序中将梵学定义为“基于梵文文献的古典印度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梵文研究确立了基调。自200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便着手推进特殊学科建设项目,其中一项核心任务便是对那些濒临失传的“绝学”学科进行立项支持,梵文研究便在其中。
多举措推动梵文研究发展
梵语是印欧语系语言,与人们熟悉的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拉丁语属于同一个语系,与古波斯语等同属印欧语系之下的伊朗语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姜南向记者介绍,印欧语系正是18、19世纪西方学者发现梵语并通过比较研究确立的。作为典型的屈折语,梵语形态变化的丰富程度堪称世界之最,甚至超过同语系的其他古代语言(如拉丁语、古希腊语)。或因长期口耳相传、不立文字的特点,梵语无论在发音、词汇还是语法上都相当精密完备,且语法结构关系可以通过词形变化精准表现,而且词汇非常丰富,可依韵律节奏灵活变换用词。因此,梵文识读第一关就要有词语拆分、拆解能力,并且能根据连音规律将词形还原成其原形,才能识别出该词语。
“中国历代求法僧人和学者的西行记录,为读解印度古代文献尤其是梵文文献,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佐证,从而推动印度古代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助理研究员黄怡婷谈道。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15世纪,梵语始终是印度统治阶层专用的语言,是印度古典文学、哲学和宗教文献的主要载体。即便在15世纪之后,梵语的地位逐渐被新兴方言所取代,但对印度语言的贡献仍旧不可忽视,众多词汇被广泛吸收和使用。梵语不仅是沟通的媒介,更是文化的载体,诸如吠陀、《森林书》《奥义书》、法经、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由迦梨陀娑等创作的古典文学作品等梵语文献,构成了印度从上古到中世纪约3000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中国学者而言,梵文就是理解印度历史与文化的钥匙。
中国与印度这两个文明古国拥有长达两千多年的交往交流史,而语言是交流的桥梁。深入分析、研究两国交流史,探讨世界文明互鉴,都离不开对古代语言的深入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刘祥柏表示,在中印两国交流史上,佛教东传进入中国,两千多年来大量佛教典籍被翻译成汉语、藏语、西夏语、回鹘语、蒙古语、满语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这些古代汉语或古代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些历史文献及其古代语言现象,对于今天人们了解认识与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具有巨大且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破解古代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以及语言间影响与演变发展的密钥。
中国当代梵文研究,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两大重镇。其中,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系统开展梵文研究的学术机构,梁漱溟、陈寅恪、胡适、汤用彤等学者在印度哲学、佛教学、中印文学与文化交流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为中国的梵文研究开辟了道路。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成立后,就成为中国梵学研究的另一重镇。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的成立,一批杰出的梵文学者汇聚于此:吕澄以其在佛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而闻名;王森在藏传佛教和佛教逻辑学(因明)方面的研究成就显著;吴晓铃则翻译并介绍了印度古典戏剧《龙喜记》和《小泥车》,是印度古典文学研究的先驱。此后,多名北京大学梵语巴利语专业毕业生的加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1978年以后,曾在印度深造、长居并主治哲学与宗教学的徐梵澄和巫白慧也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梵文研究带来了新的气象和活力。
21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梵文学科已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一方面,老一辈学者人数越来越少,研究经费欠缺,研究领域曲高和寡,关注度不高;另一方面,梵语、巴利语的高门槛使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整个梵文领域后继乏人,成为真正的“绝学”学科。
为推动我国梵文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采取主动扶持政策,2008年启动“特殊学科建设工程”,将梵语文学等4个与梵文相关的项目纳入该项工程,为梵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费支持。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成立,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将梵文作为冷门绝学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梵文研究中心在外文所黄宝生的带领下,整合院内梵文研究力量,承担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梵文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202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登峰战略”梵文学科项目,外文所常蕾担任项目负责人;同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新成立梵文与南亚文学研究室,梵文学科的建制得以进一步确立。建制和课题的确立为冷门“绝学”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冷门绝学’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培养人才。” 常蕾回忆道,自立项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断摸索建立“小而精”的人才培养方式。2007年夏至2009年夏,黄宝生先生带领外文所和北京大学的数十位学员精读梵语文学和哲学经典。2010年9月至201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开设为期三年半的梵文研习班,由葛维钧、郭良鋆和黄宝生三位老师负责授课。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多所高校的70余名师生从天城体字母开始学习,掌握梵文后直接精读巴利语经典。实践证明,关注培养因研究需要而受内在驱动的梵语学习者,是“冷门绝学”人才建设中另一条卓有成效的新路径。
培养人才的工作若要持续,完备的教材必不可少。目前,国内以汉语为母语的自主性梵语和巴利语教材仍处于空白状态,这成为培养人才的一大难题。同时,国内能够教授这两种语言的老师极为稀少,短期内难以改变这一现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黄宝生、郭良鋆和葛维钧三位研究员带领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开创性地撰写并出版了梵语和巴利语的系列研究性教材。这些教材包括《巴利语读本》《实用巴利语语法》《梵语入门》《梵语文学读本》《梵语佛经读本》以及梵汉对照读本《罗怙世系》。教材内容以文学作品为主,涵盖宗教学、哲学等学科,注解方式独特,逐字逐句拆解还原语法变化、标注语法形态,并以直译的现代译文呈现梵语句法结构。这套从初阶到高阶的梵语学习教材,为梵文学科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相较于国内其他高校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梵文研究具有独特优势。梵文研究作为一门“文化价值独特、学术门槛高、研究难度大、研究群体小”的冷门学科,其语法复杂性及典籍研究专业性有目共睹。目前,国内真正能运用梵文开展学术研究的机构和个人屈指可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和北京大学南亚学系则具备团队优势。外文所梵文团队以梵语经典为依托,在探究印度古典梵语文化传统时,深入挖掘中印文化传统的交流与影响,揭示双方的差异与互鉴。该团队在梵巴语教材体系构建、梵巴汉佛经对勘研究、梵语文学经典翻译与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为梵文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继往开来翻开梵学研究新篇章
在中国学术界,梵学研究正迎来新的发展阶段。目前,当代中国的梵学研究者已在梵文经典文本翻译、梵汉语言对比研究、梵语文学与佛教文献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梵文经典作品的翻译与解读是国内开展梵学研究的基础,在长久积累中其优势也不断显现。季羡林和金克木两位学者以其卓越的翻译成就,树立了学术典范。他们翻译的史诗《罗摩衍那》、故事集《五卷书》、戏剧《沙恭达罗》、长诗《云使》以及《摩诃婆罗多插话选》等作品,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黄宝生等学者继承前辈衣钵,经过17年努力,完成《摩诃婆罗多》中译本全六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成立后,推动了梵语文学研究,出版《梵语文学译丛》16种图书,涵盖印度古典梵语文学主要文类,为中国读者了解印度古典文学打开了新窗口。在此基础上,中国梵语古典文学研究取得显著进步,季羡林、金克木、黄宝生等学者的著作成为该领域重要成果。
中国梵学研究在文学理论文献的译介和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金克木的《古代印度文艺理论文选》首次全面将印度古代文学、文艺和美学理论介绍给中国学术界。黄宝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其《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增订本)译出了10部印度古代诗学代表著作。黄宝生还撰写了《梵汉诗学比较》并整理再版了《印度古典诗学》,将印度古代文学作品和理论置于中国诗学的比较视野中进行深入分析,成为中印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
以多语种佛经文献为基础开展的佛教学和佛经对勘研究,同样是国内梵学研究的一大特色。“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黄宝生先生的《梵汉佛经对勘丛书》正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开创的研究新路径,为中国的梵文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远认为,通过梵语原典读解佛经不仅是中国古代译经活动的延伸,也是现代佛学研究的必然走向。黄宝生先生利用梵语佛经抄本或校勘本,对照汉译佛经,厘清经典文本源流,并提供现代汉语译本。这项工作有助于把握印度佛教的原始形态,研究汉译佛典,阐明佛教义理,读解梵语佛经,校勘写本文献,研究佛教汉语及语言哲学、佛经翻译史和翻译理论。黄宝生先生的研究不仅深入理解异域文化,还发挥了中国学者在比较文化领域的优势。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为佛教文献的欣赏和细读提供了独到的视角,将佛教文献的宗教意味转化为历史文化背景下的隐喻,其语言优势也为他读解佛典提供了客观的视角。
此外,中国佛经翻译历经千年,成就卓越,其规模和影响力在全球文化交流史上独树一帜。通过多语种文本对勘方法,研究者能够追溯原典,为佛经译本提供精确的标点和注释,提升佛教文献整理和研究水平,同时促进梵文佛经抄本的整理,支持印度古代文化的保存与研究。自2010年起,黄宝生先生推出了11部《梵汉佛经对勘丛书》,另有2部即将出版。这些著作包括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的《入菩提行论》《入楞伽经》等,为佛教语言和中国佛经翻译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这些成果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佛教经典的理解,也为比较文化领域的研究发挥了中国学者的独特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韩廷杰强调,目前流传下来的佛经原始语言绝大部分由梵文写就,因此要准确理解佛经,必须使用梵文。在对一些梵文佛经进行研究并与汉文佛经对照时,他发现完全符合梵文原典的佛经并不存在。因此,在研究梵文佛经并把梵文佛经译成现代汉语的过程中,无论参考什么译本,都必须通过相关语法分析厘清翻译逻辑。
对梵学的研究,离不开对印度古代哲学经典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各具特色,中国哲学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方面表现突出,印度哲学则在形而上学和解脱论等领域有深刻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成建华说,佛教传入中国后,大量梵文经典被翻译成汉文,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涵,并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催生了新的思想高峰。例如,宋明理学在吸收儒家与佛家思想的基础上,特别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身工夫论等方面,展现出儒释合流的痕迹,并产生了新的思想理论创造。梵文哲学经典的引入,不仅弥补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某些不足,还激发了中国哲学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汉语学界的印度哲学研究,被业界戏称为“做饭从种稻子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范文丽表示,汉语学界的印度哲学研究需经历校勘、翻译、义解、哲思四个环节,环环相扣,逐步深入。在开展这些工作前,还需熟悉相关文本及思想史背景。经过几代学人努力,中国的印度学、梵学学科已发展百年,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不断充实,专题性文本解读和思想家研究成果丰富。近年来,现代技术对梵语佛典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降低了梵语学习门槛,网络上丰富的学习资源使更多人能够接触和学习梵语,而且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研究工具和资料,如数据库和检索工具等。互联网的便捷使得梵语哲学典籍研究成为全球协作的工程,新生代学者在继承国内佛教知识传统和季羡林、金克木等前辈的印度学、梵文研究基业的同时,也受益于全球近两三百年的研究成果。
与国内相比,目前,西方学界对印度学的研究呈现衰落态势,但仍旧热衷于发现并研究新材料。西藏、新疆和中亚等地发现的梵文写本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国内由于写本资料封锁、梵文专家匮乏等原因,西藏梵文写本内容研究进展缓慢。北京大学南亚学系藏学研究中心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但国内其他学者难以接触写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学者屡有斩获。
中印两国作为具有区域性、全球性影响力的密邻,对于亚洲的稳定和发展、全球的和平与繁荣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印两国历史悠久,都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丰富经验,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源远流长。国内的印度学佛教学研究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进入梵文写本、文学、宗教哲学和语言等各个领域,为延续中印文明交流这项伟大事业添砖加瓦。
让梵文研究不“冷”不“绝”
众所周知,历史上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汉文大藏经,堪称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汉译佛经主要译自梵文。印度古代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留存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文献典籍可谓世界之最,值得从文学、宗教学、哲学、神话学、语言学等方面进行研究,所以需要多方面的人才,特别是梵汉兼通的高水平人才。而研究利用好汉译佛典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学者不可推脱的责任。
成建华认为,中国的梵文经典研究可以追溯到两个主要的历史脉络:一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传统的溯源性探索;另一方面则是自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入,逐渐形成了中国的近现代梵学、印度学研究传统。其根本动因,是近现代西方社会基于印欧文明寻根以及探索东方智慧的冲动。在继承这两大传统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将梵文研究与当代文化建设紧密联系,如何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找到梵文经典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只有通过这种思考和实践,梵文研究才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中焕发出活力,才能不断发展、薪火相传,保持其学术生命力。
梵语是印度古代主流语言,语法之复杂世所公认;梵文典籍卷帙浩繁,梵文写本字体变化繁复,研究专业性极强;因梵文学科的冷僻性,国内相关的研究资料相对不足,这些特点决定了梵文研究的成果很难一蹴而就。老一辈学者如陈寅恪、汤用彤等人虽力陈梵文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也遗憾人才难得,研究不易推进。如今,学习梵文的学者虽日渐增多,但是国内具有相关研究能力的学者仍然非常稀有。可喜的是,随着国家和我院的重视,“冷”和“绝”的状况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学科建设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常蕾表示,国内关于梵语文学、语言、写本、多语对勘的佛教研究将会成为梵文研究的重点领域,深入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探索中印文化交流、融合的动态过程,为探寻中印文明交流、挖掘文明互鉴的重要价值提供有力的范本。
目前,中国研究梵语文学的学者较少,研究宗教哲学的更多,尤其是佛教。然而,这些研究领域都需要对梵文的精通和掌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党素萍强调,梵语语法复杂,传统学习方式难以快速掌握,需长期磨炼才能深入理解和精准表达。学习应从基础散文入手,熟悉语序后再读诗歌,逐步涉猎不同文体,才能体会到印度修辞的登峰造极、诗歌声律之美以及印度的哲理与思辨传统。遍读经典,体会印度文学的特色,体察印度哲学概念,理解印度文化传统,从原典入手,更需潜心多年。
梵文研究离不开对梵文原典的分析研究,离不开梵汉语言之间包括梵语与其他民族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在刘祥柏看来,未来应加大对梵文原典的数字化和数据化处理投入,长期部署梵汉、藏汉对勘等逐词分析研究模式,建立全面深入的数据库和语料库,涵盖敦煌梵文写卷等出土写本和贝叶经。同时,将人才培养和项目推进纳入梵文研究的长期规划,整合梵文、巴利文、佉卢文等原始典籍的整理、对勘、建库等研究项目。继续培养涵盖语言学、文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医学等多学科的梵语人才,逐步构建完整的梵学学科体系。这将为中印古典学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梵文研究要走向深入,离不开一代代学者的传承与努力。谈及未来的工作,姜南认为,尽管国内梵文学习和资料获取已相对便利,高校和研究院所的后备力量也在增强,但面对艰涩的梵文文献及其承载的古代文明,仅靠短期梵文学习难以胜任高难度研究,人才缺口仍是梵文研究面临的最大挑战。此外,国内梵文研究缺乏统筹和协调,呈现分散状态,导致成果交流共享不及时,且缺乏统一评判标准,优劣难辨,严重制约了梵文研究的发展。因此,整合现有研究力量,围绕重点课题开展项目合作,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或为良计。
中国与印度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共同占据了全球人口总量的35%。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一直致力于追求人类社会的仁爱与和谐。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在访华时曾提倡加强中印文化交流,共同推动东方文明的复兴,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在梵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为中印文明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深度。梵学不仅是印度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促进中印文明交流与理解的重要纽带。通过梵文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索两国文化的共通之处,促进学术合作与文化共鸣,共同开启中印文明交流的新篇章,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