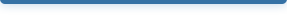本报记者 孙美娟
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适用地区主要有中国境内的藏族人,以及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境内的部分人。在汉藏语系诸语及中国各民族文字中,藏文的历史长度、文献丰富程度都仅次于汉文。
古藏文,一般指具有古藏文特点的各类文献典籍,包括敦煌写卷、钟铭、碑刻、简牍、“伏藏”文献及各类文献典籍。古藏文在浩如烟海的藏文文献中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在语言、历史、宗教、地理、生态和医学等研究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还是研究和了解古代藏族历史和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为深入了解古藏文的创制背景与发展历程,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东主才让和吉毛措。
古藏文的创制背景与深远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藏文是在什么背景下创制的?其创制的过程是怎样的?
东主才让:藏文是由“吐蕃七贤臣”之一吞弥·桑布扎创制。吞弥·桑布扎成年后,时值吐蕃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经略吐蕃,宏展其雄心抱负。由于民族间的交往、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以及治国理政的迫切需要,松赞干布深感缺乏文字的痛苦,遂在7世纪上半叶从几百名臣民中严格挑选出吞弥·桑布扎等16名聪慧优秀的青年,前往天竺拜师求学,学习梵文和天竺文字。
最后,其他15名青年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人世,唯有吞弥·桑布扎带着师长们的深情厚谊和梵文知识学成回到吐蕃。遵照松赞干布的意愿,他以梵文50个根本字母为模本,结合藏语言特点,创制了30个藏文辅音字母,又从梵文的16个元音中造出4个藏文元音。与此同时,他还从梵文34个子音字中,去除5个反体字、5个重叠字,增加了几个新的音位字母,补充了梵语的迦、恰、稼、夏、哈、阿(音译)等6个字,制定出有4个元音及30个辅音的藏文。如此依照梵文模本创制的藏文,一直沿用至今。
每种文字创制之初都不可能十分完善,需要在运用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规范、日益完善,藏文同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据藏文史籍记载,藏文在历史上曾进行过3次较大规模的厘定规范,分别在8世纪中叶至9世纪初叶、9世纪中叶和11世纪初叶。藏族历史上的几次文字改革,采取了调整藏文字母体系、简化正字法、规范词语和语法,确立藏文字的书写法,并立法推行等措施,不仅促进了藏文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还对藏文的统一和推广应用,以及藏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藏文有何独特之处?
东主才让:藏文书写习惯为从右向左。字体分两大类,即“乌金”和“乌梅”,是根据字体的不同形式而得名。乌金相当于楷书,常用于印刷、雕刻、正规文书等;乌梅相当于行书和草书,主要用于手写。乌梅又可细分为“粗通”(tshugs-thung),意为“笔画短促”;“粗仁”(tshugs-rin),意为“笔画长”;“珠杂”(vbru-tsa),是一种笔画转折处棱角突出的行书字体;“丘”(vkhyug),适合速记,其形体与印刷体差别甚大。
藏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属辅音文字型,分辅音字母、元音符号和标点符号3个部分。其中有30个辅音字母、4个元音符号,以及5个反写字母(用以拼外来语)。藏文字形结构均以一个字母为核心,其余字母均以此为基础前后附加和上下叠写,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字表结构。此外,古藏文标点符号形体简单、种类极少,而且使用规则也与其他文字的标点符号有别。其标点符号共有6种形式,其中音节之间的隔音符号使用频率最高。此外,还有云头符,用于书题或篇首;蛇形垂符,用于文章开头处;单垂符,用于短语或句终;双垂符,用于章节末尾;四垂符,用于卷次末尾。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便于更加准确地表达语义,藏文中已开始借鉴并使用汉文等现代通用的标点符号。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藏文在文化传承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对后世有何重要影响?
东主才让:据记载,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后,藏族地区开始掀起学习藏文的热潮。松赞干布亲自组织翻译、学习、借鉴印度和汉地的文化,开启吐蕃人的智慧,哺育造就了像噶尔东赞等一批作出突出贡献的名人志士。松赞干布也因此有可能创立“三十六制”等吐蕃法律,藏族社会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文明的崭新阶段。
吞弥·桑布扎不仅在藏语言、文法上颇有创造研究,同时还是一位翻译家。他撰写了《文法根本三十颂》《文字变化法则》《文法性之法》等8部语言文法著作。在1300多年前能写成如此严密的语法学著作是难能可贵的,不但在中国遥居首位,在世界语言学发展史上也是发始较早的。与此同时,他翻译了《二十一显密经典》《宝星陀罗尼经》《十善经》《般若十万颂》《宝云经》《宝箧经》等20多种佛经,藏族历史从此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
深化古藏文研究意义重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我们为什么要推进古藏文这种古老文字的研究?
东主才让:推进古藏文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古代藏族社会、增强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具有重要意义。古藏文包括金石铭刻(碑文、摩崖石刻等)、文契简牍(封文、令旨、契约、书翰及出土写卷、文件残页)和书籍卷册(各类史书、史传、志书及年表、大事记等),这些古藏文文献蕴含着丰富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的思想。
比如,在敦煌写卷中有一种现象,即以藏文字母对汉语文字、词汇进行注音,如同汉语拼音一般,甚至用藏文字母拼写汉文文章、文书、诗词等。如藏文全文注音出现在《九九乘法口诀》《千字文》《藏汉对照词汇表》等写卷中,以及一些经书、计算类典籍等书籍中。此外,在古藏文《大宝伏藏》等伏藏文献中有九宫、八卦、阴阳五行、十二属相、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甲子周年等有关上古汉文化的内容,且为数不少。此外,敦煌藏文文献中不仅出现较多的汉族姓氏,还出现有麹等高昌国姓氏,安、曹等粟特人姓氏,尹、齐等羌族姓氏,名则用藏族人名,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上述民族逐步接受了中原文化。
通过对这些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和姓名变化的分析研究,探讨吐蕃时期敦煌地区语言文字在文化交融中的作用,以此探究汉藏文化及各民族互相交流影响的深层逻辑。这种古藏文语言文字的使用特征和文化所衍生的汉藏语言文化交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例。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我国古藏文研究处于怎样的状态?与国外古藏文研究相比,我国古藏文研究是否处于优势?
吉毛措:我国对古藏文文献的大规模诠释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90年代达到高潮。国内对古藏文文献,特别是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研究成果数量很大。主要代表人物有我国藏学家王尧、陈践等学者。他们通过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的编目、整理和释读,使得许多沉睡千年的古文献得以重见天日。
近年来,与国外古藏文研究相比,我国古藏文研究在某些方面占据了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内对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已形成较为全面的体系,为古藏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文献资料;其次,近年来,我国对包括“古藏文文献”在内的冷门绝学学科扶持力度加大,关注度比较高,促进了古典学、敦煌学和古文字学等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再次,在21世纪前20年里,各种民族史研究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单位相继成立,培养了一大批古藏文研究的专门学者,并产出了大量的学术成果。
但是,国外的古藏文研究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起步较早,基础研究扎实,特别是近年来的学术论文,研究视角独到,方法新颖,影响深远。另外,国外在古藏文基础资料的数字化和应用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从图像到文字检索以及主题联想检索,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国内在这方面还有待加强。因此,国内与国外古藏文研究相比,各有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报》:受语言障碍、历史文献分散以及地域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藏文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一块“硬骨头”。您觉得,古藏文研究“难”在哪里?该如何突破?
吉毛措:古藏文文献主要涵盖吐蕃时期遗留的碑刻钟铭、木简以及敦煌藏文写卷等三大类别。研究古藏文时,我们需认识到它与现代藏语之间存在差异。研究者并非只要略懂藏文或涉足藏学研究,便能胜任古藏文研究。实际上,藏学界对古藏文有着严格的鉴别方法和标准,这些标准基于文字的古老性和历史年代。正如我国古藏文学者陈践所指出的,“在研究古藏文时,切勿将‘古词’完全等同于现代藏文的‘正字’进行解读,而应自觉运用安多方言和民俗资料”。因此,进行古藏文研究,不仅需要有深厚的学科知识和扎实的藏文功底,还需要耐得住寂寞,才能深入并扎实地推进研究工作。
上述三大类古藏文年代久远,大多数手稿遭受严重损坏,加上藏文书写缺乏统一标准,使文字辨识变得复杂,进而引发了众多学术难题。此外,古藏文文献中的词汇和句法与后期文献存在显著差异,尤其在社会文献中,许多术语在后期文献中难以找到对应项。因此,学者们通常只能依据古藏文文献的语境和使用背景进行推测和考证。但由于个人知识结构的差异,学者们对古藏文中的疑难术语往往持有不同见解,难以达成共识,更难以深入探究其含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虽然古藏文研究存在诸多困难,但是我院对其研究高度重视。请您谈谈,当前我院古藏文研究的现状如何,都有哪些人在做古藏文方面的研究,院里对古藏文研究有何扶持政策。
东主才让:古藏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我院历来非常重视冷门绝学学科发展和传承,曾涌现出王森、牙含章、邓锐龄、柳升祺、王静如、安世兴等诸多从事西藏研究的学界前辈,为藏学研究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院里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有不少涉及古藏文研究,例如《吐蕃历史编年》及《赞普传记》的汉文译本在20世纪50年代由我院学者王静如译出,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西藏历史调查组打印内部发送,这是国内最早的汉译本。此外,我院学者安世兴为语言学和古藏文学专家,在民族所几十年的工作中专门从事藏语语言学和古藏文研究,取得很多成就,研究成果有《古藏文词典》《藏文缩写字典》《评介古藏文词书丁香帐》《古藏文音变几例》等。
吉毛措:当前,我院有我和东主才让老师在做古藏文研究。东主才让老师曾参与编纂《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图版)、《北京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整理与编目工作。这些工作涉及大量文献的定名、定性以及编目,任务艰巨且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外,东主才让老师还参与和主持我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特殊学科(绝学)“古藏文”项目等多项社科项目,目前已完成编辑整理63函/册全套《大宝伏藏》文集、编纂《藏汉对照大宝伏藏目录及题跋》以及编辑完成古藏文伏藏文献数据库资料等工作,为古藏文文献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对于古藏文研究的扶持政策,我院不仅有“特殊学科(绝学)项目”“登峰学科建设资助项目”“冷门绝学学科”等学术工程项目,还专门设立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古藏文文献整理研究”。这些政策为古藏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继往开来书写古藏文研究新篇章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社科院人才培养工作计划要求,2019年,您博士后刚出站就被引进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藏学与西藏发展研究室工作。近五年来,您在古藏文研究方面有何新进展?
吉毛措:2019年,我入职社科院后在藏学与西藏研究室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在工作中,我不仅参与了社科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古藏文文献整理研究”项目,先后出版了《噶塘蚌巴奇苯教古文献研究》《嘉绒金川勒乌摩崖石刻》,其中《噶塘蚌巴奇苯教古文献研究》是目前唯一一部关于21世纪初在西藏境内出土的古藏文文献的专题研究成果;还参与了导师的课题,搜集、整理和校注了《古藏文手抄珍本文献》(10册)。此外,我还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个人专项一项,即翻译和研究西藏境内出土噶塘蚌巴奇苯教古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古藏文研究的前辈学者,您认为未来古藏文的研究方向和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您对古藏文文献研究有什么建议?
东主才让:“伏藏”文献是未来古藏文的研究重点。“伏藏”文献是吐蕃时期莲花生大师和藏族先辈写好后埋藏起来的,后因发现其多被埋藏在地下与其他隐蔽处,故称“伏藏”,发掘者被称为掘藏师、伏藏师。古藏文伏藏文献《五大藏》《大宝伏藏》等系列文集是史无前例的集西藏佛教和传统文化于一体的著作,对整个藏族历史、文化、藏传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古藏文伏藏文献存量很大,大量文献尚未搜集整理,国内外也尚未对其展开全面研究。伏藏作为藏族历史文化中的一种特殊文献,急需学者研究了解,也应该是古藏文文献今后研究的方向。
对古藏文文献研究的建议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对古藏文文献研究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古藏文古籍的保护工作。尽管我们对古藏文文献研究出台了很多扶持政策,但仍有待完善。例如,目前,我做的《大宝伏藏文集》的整理与研究约1300万字,已全部完成编辑、校勘和编纂目录题跋工作,却仍面临出版经费不足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目前,我院在职人员除了您并无其他人在研究古藏文。您认为,未来,您要如何做才能传承先辈精神,让古藏文研究绽放出新光芒?
吉毛措:目前,我是唯一在职且专门从事古藏文文献研究的科研人员。显然,古藏文的研究对社科院来说已经成为“冷门”。我认为,新时代做好古藏文研究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紧扣时代脉搏,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基于此,未来我将从三个方面开展自己的工作:第一,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视角,以多角度和多学科交叉的方式,力争出一些古藏文研究方面的学术精品。第二,培养学生,壮大古藏文研究团队。第三,搭建古藏文文献研究中心,通过这个平台深挖古藏文文献中符合时代要求和工作主线的相关内容,努力使得“绝学不绝”“冷门不冷”,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