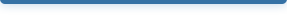发掘以古文字重建古史的应用价值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文字学”学科带头人冯时
古文字学是研究先秦时期古体文字的学科,涉及文字起源、古文字学的基本理论、文字释读、甲骨学、金文学、战国文字学、早期民族古文字学以及古文字与古史研究等重要课题。文字是承载中国文化基本概念的符号载体,作为连接古今文明的桥梁,古文字学研究的深化,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及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绝学)”第一批名录,古文字学位列其中,予以重点扶植。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学科“古文字学”学科带头人冯时,了解近年古文字学的发展趋势和学术成果,以期深刻认识古文字对于传承文化和重建古史的重要作用及其学术价值。
重新界定古文字学范畴
《中国社会科学报》:冯老师好!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古文字,古文字又是如何识别的?
冯时:汉字的书体一般分为真草隶篆四种,而古文字与今文字的区别就在篆隶之别。这一概念在西汉就已形成。汉代的古文经是指以先秦古文字写就的经学文本,而今文经则是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就的文本。所以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先秦时代的古体汉字。然而在文字隶变过程中,早期隶书尚未摆脱篆法结构,因此隶书的结体对于古文字的释读仍然具有一定意义。其实,如果我们规范古文字的概念,它主要就应指秦以前的古体汉字,当然也不能不关注早期隶书材料。同时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必须强调,传统意义上的古文字是指古体汉字,但考古学提供的资料打破了这种成见,它表明中国的上古文明并非汉字一统,同时存在的还有东夷文字,准确地说就是今日生活于川滇黔桂的彝族的古文字。这意味着古文字学研究必须包括早期的民族古文字学,这不仅彰显了中国文字起源的多源特点,而且从根本上解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渊源。
具有了这样的认识,古文字学就不应该再被理解为仅仅是对古体汉字的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也不能理解为仅仅是指汉字的起源,这使考古学在古文字学研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简单来说,早期文字多源于象形,但在不同的文字体系中,相同的象形符号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正确地释读古文字,特别是处于文字起源阶段的早期文字,首先就必须通过考古学研究明确相关文字的文化属性,然后才可能以相应体系的文字对比识读。今天的研究成果显示,古夷文于距今8000年前就已形成,而确凿的汉字也已有了至少7000年的历史,这为印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坚实物证。
明确了文字体系,就可以对文字进行考释。唐兰先生曾提出考释古文字的四种方法,即字形的因袭比较、辞例推勘、偏旁分析和历史的考证。我自己补充二法,即以古文字形体演变规律释字及审音求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根据您的介绍,古文字其实包括了很多文字类型,那么古文字的分类具体有哪些?
冯时:古文字分类可有不同的观察视角。如从文字体系的角度,可分为夷、夏和巴蜀文字,夷文字是今日彝族的古文字,夏文字是汉字的祖先,巴蜀文字的性质还不清楚,可能有对夷夏文字的借鉴。从时代的角度判断,可分为新石器时代文字、三代文字、战国文字和秦篆。从文字的载体分类,又可分为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陶文、石刻、封泥、货币等,当然,每一类材质的文字又有早晚时代的不同。
传统分类的甲骨学、金文学都体现着材料和时代相结合的意义,如甲骨文向以为专指商代文字,这种理解虽然从商代甲骨文的绝对数量上说不错,但今天的新发现却使甲骨文已不再局限于商代,不仅西周出土了甲骨文,而且更见新石器时代契刻于龟甲上的古夷文,距今已逾8000年,这些史料极大拓展了甲骨学的研究范围。再如古玺文字,尽管东周以后普遍流行,但考古不仅发现了西周古玺,更发现了商代古玺,虽然早期发现的三枚商代印章并非考古发掘所得,但近年殷墟考古新获得的三枚商代印章证明了早年发现的真实性,所以印章的历史也非常悠久。从这个角度思考,其他载体上的文字又何尝不是如此。陶文从新石器时代以降普遍存在,而随着考古学的发展,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其时代也都存在着超越原有认识的可能。
战国文字学的独立分类主要考虑了时代概念,原因就在于这一时期的文字表现出了显著的地域差异。《汉书·艺文志》:“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战国时代不仅六国文字与秦不同,而且六国之间也不相同,时代特征鲜明,这促使秦始皇不能不采用书同文的措施。将战国文字与秦文字进行比较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它使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秦书同文的具体措施。
古文字学的分类应该适应相应的时代和材料,夏王朝之前应该建立夷夏文字的分类标准,而夏之后,则应将时代和材料综合考虑。当然,古人对于古文字的分类也值得参考,《汉志》有秦书八体,《说文解字叙》有新莽六书,皆以书体的不同用途为分类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报》:许多学科对古文字都有所涉及,比如语言学或历史学,在考古学领域,古文字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冯时:古文字研究在不同的学科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学术目的和研究方法也因学科而异。纳入历史学和考古学范畴的古文字学研究,目的自然与单纯的文字学、语言学或艺术史研究不同。历史学研究中的古文字学是要利用古文字材料解决历史问题,而考古学更将古文字学作为其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成为阐述考古学文化与考古遗存的认识基础和诠释方法。因此,尽管古文字释读是古文字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但服务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古文字学研究却不以文字的识读作为最终目标,而是旨在以古文字材料作为史料,利用其重建古代社会的历史。
史料对于重建古史而言,其价值有高下之分。最重要的当然是直接史料,其次是基本史料,再次是辅助史料。古文字材料由于直出先民之手,基本上都属于直接史料,对于重建古代社会的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当然,某些战国竹书见有后人追溯古史的记载,不可避免地留有后代的史观,其与直接史料应有所区分,需要认真鉴别。
中国先贤以古文字材料证经补史,深具传统。汉出先秦古器,唐见先秦石鼓,时人皆据以论古。至北宋金石学创立,出土的古器碑版更得到了系统整理,学者考索文字,证经补史,使金石学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事实上,考古资料的价值各有不同,其中的文字材料对于判断遗存性质发挥着独特作用。如殷墟文化性质的证认主要即因有甲骨文的发现,从而证明商王朝存在这一不可动摇的事实。西周封建制度的确认也因各诸侯国具铭铜器的出土,最终构建起西周王朝的天下格局。同样,夏王朝存在的事实也将因夏文字的发现而终被证实。所以古文字学研究对于考古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古文字学素称“小学”,其为经学、史学之本,经国济世之基。所以对古文字学的深入研究不仅有裨于历史学与考古学重建古史的工作,更有裨于中国文化的传承,这便是古文字学核心价值之所在。
以古文字学解密先秦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在什么契机下投身古文字学研究的?
冯时:我对古文字的爱好始于少年,初中时代,我师从尹瘦石先生学习书法绘画,逐渐对古文字产生了兴趣。后来在蔡美彪先生那里看到他年轻时师从王襄先生学习甲骨文所做的摹本,很受感染,对古文字的兴趣也逐渐浓厚,于是找来郭沫若先生的书看,并立志以此作为终生的事业。
我的学术初心非常明确,那就是学习古文字,所以在报考大学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作为第一志愿,因为在那里可以系统学习古文字。幸运的是我被录取了,并在毕业后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将爱好与工作结合起来,不断探索进取。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特殊学科建设工程”,古文字学被纳入其中。当时研究面临的困难是什么?纳入“工程”后为古文字学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
冯时:我一直以为,学科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人才,人在学科就在,没有足以支撑学科的人才,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所以,人才的学养和能力决定着学科的现状和未来,学科拥有了有能力开创事业的人才就能屹立不倒,反之则必然消亡。对于考古所的古文字学科而言,这一问题尤其突出。考古所的古文字学研究之所以成为传统学科,原因就在于薪火相传。由于夏鼐先生的重视,先后出现了以陈梦家、王世民、陈公柔、张亚初、刘雨、刘一曼为代表的一批学术前辈,支撑起了考古所古文字学科的一片天空。
老一辈学者不仅专注于殷墟发掘和古文字资料的整理,更将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相互结合,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如陈梦家著《殷虚卜辞综述》,刘一曼等编著《小屯南地甲骨》《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王世民等编著《殷周金文集成》,张亚初编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具有划时代的贡献。我自己则主编《金文文献集成》,著有《中国古文字学概论》。这些成果具有考古所古文字学研究的鲜明特色。
然而随着老一辈学者的辞世和荣休,后辈人才并没有得到及时补充,以致现在考古所古文字学学科队伍有些青黄不接。如何让青年学者迅速成长,并且具有兼跨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研究的学术能力,继承古文字学考古学派的学术传统,是考古所古文字学学科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适时筹划“登峰计划”,启动“特殊学科建设工程”,对考古所古文字学的学科建设非常重要,尤其对于年轻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古文字学的图书价格昂贵,学生难以承担,而资助的经费可以使学生放心购买他们需要的图书资料,考察调研,增广见闻,安心治学,成效显著。
经过多年的辛勤培养,确有一批出色的学术人才脱颖而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后学都没有机会留所工作,终成考古所古文字学科建设的巨大损失。人才培养是一项长周期的艰难工作,并不是每一位从学者都能成为堪当重任的学术人才。对于真正的学术人才不可错失,这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直以来,您都致力于古文字学研究。近年来,古文字学领域有哪些重要发现或代表成果?
冯时:新发现的古文字材料往往决定着新的学术课题和学术方向。以清华简的《保训》为例,它的发现解决了中国文化至为关键的地中变迁的重大问题。
“中”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中国文化何以传承数千年没有中断,关键原因即在于恪守着“中”的观念。“中”于天下空间的认知就是天地之中,古代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其以王朝论天下,王庭必建于天地之中,如此才具有政治和宗教的合法性,成为正统王朝,居中而治者当然也就肩负起了传承文化的使命。所以中国文化重在居中,而并不看重族群的更迭,形成了与西方根本不同的文化。
《保训》记载了周文王与其子姬发所讲的地中变迁的故事,这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最早的地中由舜所定,终使其获得了尧的禅位。后来商汤的六世祖先上甲微重定了地中,至汤而拥有了天下。这个地中变迁的历史不仅于传统政治史研究具有意义,而且可以通过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古天文学的综合研究得以重建。
古文字材料对于解决中国上古史的重大问题具有关键意义。早期文明夷夏东西的格局,这一认识首先即源于对古文字的研究。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时代遗址出土11字陶文,已经具备书面语特征,但非属汉字,以古彝文却可成功识读,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则是汉字的祖先。这些发现和研究证明了傅斯年早年有关夷夏东西的论证,即有夏之前,太行山以东分布着东夷文化,太行山以西则分布华夏文化。当然,相关考古学研究也支持了这种认识。
由此可见,古文字研究,尤其是文字起源的研究,必须要与考古学密切结合。没有这种结合,单纯的文字考释是没有意义的。
古文字学研究不仅可以解决大的文化格局问题,对于王朝的认定更有直接意义。夏王朝存在的事实已经显现出通过夏文字最终认证的端倪,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朱书“文邑”,证明其即为夏代早期王庭。“文邑”之名不仅见于商代卜辞,而且其名即犹商代王庭而称“商邑”或“大邑商”,证明“文”实为夏王朝的本号,其后改称“文夏”,后更称“夏”。而二里头遗址的始年不早于公元前18世纪中叶,应系夏代晚期的王庭遗存。
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对解决中华文明的重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而且清晰梳理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文脉,这体现了古文字研究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真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较国内其他研究机构,考古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是什么?与其他机构相比具有什么优势?
冯时:考古所古文字研究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作为全国唯一将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机构,我们要求研究者要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古文字不是孤立的研究对象,文字出土的地层、伴出物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考古学的分期方法也会运用于判断古文字的年代。这些考虑都将使人更全面地了解出土文献的价值。
我并不赞成过分强调学科的划分,古文字学已经是一个很小的领域了,再过分细化,必将导致研究视野的局限。全面掌握古文字学涉及的不同领域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以古文字重建古史的应有价值。
古文字学是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对解决历史问题有其独特的作用和关键意义。古文字研究不仅可以直接证明古代遗存的性质,揭示古代社会关系,而且可以作为考古材料与文献史料的佐证,使重建的历史成为信史。这种将古文字学研究与考古学、文献学乃至其他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广泛的知识,如此才能完成重建古代信史的工作。
正像考古学研究不宜过分强调其学科的独立性一样,古文字学也同样不宜过分强调其独立性。今天提倡跨学科研究,目的实际是要强化学者的综合研究能力,过分强调学科的独立性只能陷于抱残守缺。知识是相通的,人文科学尤其如此。只有以多学科视角考虑问题,才能胸有全局,认清问题的本质,这是文史哲乃至考古学等人文学科的共同追求。当然,考古所的古文字学科建设也应以此为目标,研究者应尽量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将古文字与考古学研究有机结合,建立具有考古学特色的古文字学派。
发挥古文字的当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古文字学的发展趋势?当前,您认为古文字学研究中最具挑战的问题是什么?
冯时:古文字学古称“小学”,似乎其只是研究文字形、音、义的学问。其实不然,古文字学研究实际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释字,一是考史。释字旨在求文字之本,考史则在求文字之用。考释文字的工作当然需要精通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知识,熟练掌握古文字学的基本理论。然而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角度讲,解决文字之本显然并不是古文字研究的最终目的,而求文字之用则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更广博的知识,不仅谙熟经典文献,通晓古代制度,还要对传统哲学与思想有系统了解,甚至于民族古文字学也应有基本的认知,否则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文字的深意,终将使出土文献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当然,广阔的知识储备要求研究者必须终生学习,不断丰富自己。事实上,这不仅是对古文字学研究者的要求,也是对所有中国文化和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现代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对古文字学研究的影响?
冯时:我们应该秉持一种根本的理念,那就是科技发明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而非取代人类。假如人类把认识世界的能力交赋科技或仪器,以其代替人类的思考,从而泯灭了人类的灵性,那么这种科技就不如没有。所以我主张,至少人文科学研究要有意识地与现代科技保持距离,要在科技的便捷和人类的智慧之间找到平衡。
我曾分享过一则亲历的笑谈。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如果没有导航,他已无法回家。此事令我颇感震惊,短短几年对导航的依赖就已使大脑丧失了对道路的记忆,那么长此以往,人类探索自然的能力还能所剩几何?许慎认为人是“天地之性最贵者”,强调的正是人具有超乎其他物种的灵性,而现代的某些科技难道不是在摧毁这种灵性吗?所以对待现代科技不能趋之若鹜。
电脑的便捷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以致很多人只知查书,而不知读书。读书是对书从头到尾的完整阅读,而不是仅据几个关键词了解大概。阅读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如此才能心有所得。浅尝辄止的查书虽然便捷,若一生如此,必终无所获。
《庄子·天地》有一段有关机械与机心的论述,发人深省,人怀机心,将永远不可能求得真理。先贤于机械之利弊洞彻清晰。这些古老的智慧告诉我们,过分依赖科技无疑会令人失去深入思考的能力。所以先辈告诫我们要坐冷板凳,下笨功夫,这才是求道的正途。
古文字学领域同样存在盲目追求科技的倾向,或借人工智能拼合甲骨,甚至据人工智能考释文字。机械所获得的信息并不完整,其以甲骨拓本缀合,只考虑了平面形状,却不知甲骨的真实形态,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而将考释文字的工作委以人工智能就更加危险。
对人文学者而言,科技伦理是必须重视的问题。中国传统的知识论强调伦理对欲望的约束,这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中国传统的知识论和宇宙观对今日的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最近我刚发表一文《知识论与宇宙观——现代文明的历史思考》,对这些问题有所论述。事兴一利,必生一弊,利用现代科技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利弊得失。
《中国社会科学报》:古文字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对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民族精神、丰富人类文化有重要意义。但古文字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今日我们推动古文字学发展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冯时: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绵延不绝,其核心思想即在于居中而治的政治观,而传承形式则是文字。文字的创造具有其宗教目的,其作为人神沟通的媒介,对王朝的建立和天命的确认非常重要。夏王朝诞生之后,夏文字成为人神沟通的正统文字。其后商灭夏,必须继承其文字而与神沟通,确认天命的归属。周灭商也必须继承其文字,这种对于沟通人神文字的继承确保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所以汉字并不像其他古老文明的文字那样已经沦为化石,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今天我们以学习西文的拼音方法学习汉字,摒弃六书,忽略了汉字的本义本读及其承载的文化概念。汉字是承载概念和文化的符号载体,汉字没有中断,也就意味着文化没有中断,所以学习中国文化必须从学习汉字开始,如此才能形成完整的中国文化概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