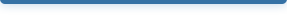新清史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兴起的研究中国清代历史的学派。1996年,美国学者罗友枝发表《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反驳何炳棣在《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对“汉化”的强调,由此又引发后者发表《捍卫汉化:驳斥罗友枝的〈再观清代〉》。这两篇文章,成为“新清史”学派出现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新清史”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新清史”学者试图将清朝与汉族王朝相区分,这不仅否定了清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贡献,也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清朝历史的复杂性。为了更为全面、客观地了解和认识“新清史”,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李大龙。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国内外学界关于“新清史”的讨论,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李大龙:从目前发表的众多论著看,“新清史”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清朝是“汉化”还是具有“满洲性”。传统的观点认为清朝虽然源于东夷的“满洲”,但一直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并通过入主中原实现了中华大地的大统一,将悠久的“大一统”历史传统发扬光大,学界一般将这一过程称之为“汉化”。而强调清朝的“满洲性”进而否定清朝的“汉化”则是“新清史”一系列观点形成的前提和基础,进而和国内外学界的传统认识形成对立。
其二,清朝是中国历代王朝的继承者还是“征服王朝”。将清朝视为中国历代王朝的延续发展,认为清朝集历代王朝之大成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构建是国内外以往的传统认识,但将清朝定位为“中国”之外的“满洲”,进而在“征服王朝”的视角下认识清朝“大一统”则是“新清史”的核心观点。
其三,“满洲”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国内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概念出现在先秦时期,但“五方之民”中的“中国”具有多重含义,建立清朝的满洲人虽然属于东夷,但在“胡汉一家”的传统观念下依然可以通过“用夏变夷”而跻身“中国”,建立秦朝的秦人、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等都是例证。“新清史”则试图通过论证清朝的“满洲性”将其排斥在“中国”之外,这也是其一系列观点形成的基础。
其四,如何认识“中国”。国内学界一般将“二十四(五)史”(包括《清史稿》)记载的历代王朝视为“中国”,而“新清史”则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认识“中国”,将“中国人”等同于“汉人”,否认清朝是“中国”,“中国”是清朝疆域的一部分。
其五,满文档案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强调利用满文文献研究清史是“新清史”一度被国内学界视为“新方法”的重要理由,但也有国内学者指出“新清史”的论著也多数依据汉文史料撰写,且利用包括满文文献在内的多语种文献研究清史一直是我国学界的传统做法。
其六,“新清史”是学术探讨还是具有政治目的。尽管在初期国内学界将“新清史”定位为“学术”,但由于“新清史”引发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清史研究的范围,甚至涉及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等原则性问题,如欧立德就明确提出了“什么是中国,中国是什么”的命题,故而将“新清史”视为有“政治目的”已经是国内学界的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清史”主张划清清代与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的界限,我们对此谬论应如何予以回击?
李大龙:“新清史”虽然是以“学术”面貌出现,并在初期似乎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同,但其对清朝历史的歪曲解读是对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传统认识的解构,政治意图是难以否认的,国内学界持续发表的大量对“新清史”的批驳论著也证明了这一点。应该说,“新清史”本质上是一种对清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别有用心”的话语体系建构,仅仅从“史料是否坚实可靠”“分析是否规范”“结论是否给人以启示”等学术视角对其进行回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其史观和利用的理论进行分析和评价,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其险恶用心。与此同时,我们更要认识到,在历代王朝和“民族国家”观念影响下,目前我们有关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话语体系还存在有待完善的问题。在传统的历代王朝史观和近代传入的“民族国家”观念严重影响下,我们很难为“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建一个完善的话语体系,以应对“新清史”等歪理邪说对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的解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否定“新清史”中“边疆是边疆,中原是中原”的观点,有哪些强有力的依据?请简要列举两三个案例。
李大龙:将“满洲”和“中国”视为两个对立的个体是“新清史”一系列观点的基础,但“边疆是边疆,中原是中原”的认识并不符合中华大地上政权和人群凝聚发展的实际,也不能准确认识和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无论是作为人群概念的“五方之民”中的“中国”、秦汉以后的“华”(诸夏、华夏、中华)和“夷”(夷狄、四夷、戎狄),还是作为“大一统”文化象征的“中国”“中华”以及地理概念的“中国”,其含义都是多重的,且涵盖的内容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将“中国”等同于“汉族王朝”、“中国人”等同于“汉族”或“汉人”,是对中华大地历史演进真实状况的歪曲解读。二是,尽管有“五方之民”,以及“华”与“夷”的区分,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二者共同构成了“天下”,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群共同缔造了多民族国家中国,而在缔造伟大祖国的过程中,这些人群凝聚成了“多元一体”具有密切血肉关系的中华民族。
“中国”的含义虽然是多重的,但在清代增加了指称“大一统”王朝国家的内容。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双方在东北亚的边界,其中有“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的条款。从将领土归属的对象分别称为“中国”和“鄂罗斯”来看,“中国”的含义无疑已经明确指向了清朝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国家,而与此同时出现在《清圣祖实录》中的“海洋行船,中国人多论更次,西洋人多论度数”,“中国人”涵盖的范围是清朝境内包括“汉人”和“满洲”在内的所有“臣民”,“新清史”将“满洲”和“中国”对立是无法对此状况进行合理解释的。
将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分为“中国百姓”和“四夷之人”虽然是一种传统做法,似乎迎合了“新清史”“边疆是边疆,中原是中原”的观点。但现实却是,在古人的观念中,二者并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这也是“天下一体”“天下一家”等表述经常见诸于史书的直接原因。《旧唐书·李大亮传》所载“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是最具有典型性的表述。李大亮用“本根”和“枝叶”构成的“树”来描述“中国百姓”和“四夷之人”的关系,既是对二者“天下一体”关系的认定,同时也形象地表明了二者关系的密不可分。
“夷狄”能否成为“天下之主”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争夺“正统”过程中的核心议题,而胜利者自称或被称为“中国”也是一个历史事实。尽管“新清史”屡屡强调清朝的“满洲”特点,而国内也有学者用很大篇幅来论证“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但清朝的雍正皇帝在其撰写的《大义觉迷录》中首先认为“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聚群分”。在此基础上则将“满洲”定义为一个地域人群的概念:“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 此表述虽然具有为清朝的“正统”地位得到认同而辩驳的嫌疑,但其“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的进一步阐述,则精准点明了属于“夷”的“满洲”和被视为“华”的“中国”共属于“天下”,是不能分割的“一体”,而“华夷”划分的出现是源自“正统”争夺的需要,和当今来源于西方的“民族”“帝国”话语并不具有相同的性质,故而从“民族国家”或“征服王朝”的视角认识和诠释中华大地上的政权兴替与人群凝聚交融的状况,是“张冠李戴”,其结果只能是得出歪曲的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涉及“新清史”的研究,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
李大龙:应该说,目前国内学界有关“新清史”的研究,虽然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回击的阶段,但根除“新清史”的影响则任重道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以“学术”面貌出现的“新清史”在历代王朝史观严重影响的当下,其有些认识依然会得到有些学者的认同;另一方面,将“夷狄”排斥在“正统”之外虽然是先秦儒家的主张,而东晋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争夺“正统”视为“五胡乱华”也是东晋南朝等为争夺“正统”而构建的话语,但在“大汉族主义”影响下还是有学者尤其是国人认同这些看法,而认为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以及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是“异族”对“中国”统治的观点也屡屡见诸于互联网。这些都说明在注重研究“新清史”史观的同时,也要关注和探讨我们当下认识和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所持有的史观,因为史观的不同是认识出现分歧的深层次根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提高包括清史研究在内的历史研究话语权,您有哪些建议?
李大龙:我国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研究话语权面临的挑战并非仅仅是“新清史”,国外学者所持有的以“长城以北非中国”为核心的“内亚”史观,以及将云贵以南的东南亚视为“无政府状态”的“赞米亚”史观等同样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构成了挑战。
当前,面对“新清史”等带来的挑战和威胁,努力实现对历代王朝史、民族史等传统做法的超越,进而构建起完善的话语体系应该是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尝试着做了一些探索:一是“中国”“中华”概念更多情况下是适应争夺“正统”的需要而出现的,表示王朝国家疆域的用语是“天下”并非“中国”“中华”,因此应该超越以往聚焦历代王朝所代表的“中国”的做法,从“天下国家”的视角审视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二是从“天下国家”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视角审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以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标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康熙二十八年之前是传统王朝国家的“有疆无界”时期,在没有域外势力进入的情况下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在“大一统”思想的引领下缔造着多民族国家,呈现自然凝聚的“有疆无界”状态;康熙二十八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通过与沙俄签订一系列边界条约,厘清了中国东北和北部的边界,“王朝国家”的疆域开始转变为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状态;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域外殖民势力进入东亚建立殖民地,和东亚以清朝为中心的藩属体系发生碰撞,多民族国家疆域遭到了蚕食鲸吞,最终形成了当今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规模。三是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概念传入之前,中华大地上有着独特的划分人群的方式,“五方之民”的划分是基础,以政权或部落的名称称呼凝聚的不同人群是常态,而出于争夺“正统”的需要,这些人群又被划分为“华”“夷”两大群体,在“华夷一家”实现着凝聚与交融,最终“自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我们在“五个共同”的指导下建立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实际的话语体系不仅是回击“新清史”的需要,更是“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